丁玲小说手稿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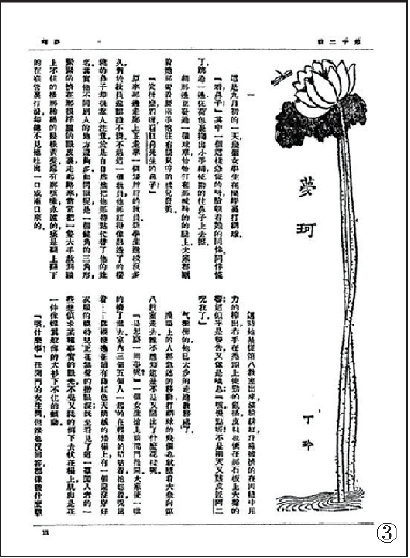
《梦珂》手稿上丁玲署名
作者:王锡荣
前不久,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丁玲小说手稿三篇》影印本,其中包括丁玲处女作《梦珂》、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早期作品《暑假中》。这些手稿,都是来自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收藏,书是由该馆和左联纪念馆合编的,这些手稿也是第一次影印出版。虽说只是三篇短篇小说的手稿,但却是丁玲早期最有代表性的三篇作品,这批手稿历经近百年的沧桑,得以完整保存,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但也充满了未知的谜。一是其来源,二是其署名,三是其修改,四是其编辑,都还有一些没有解开的谜团。
首先是它的来源。这几篇手稿,虽说是鲁迅纪念馆收藏的,但是其来源却是个谜。根据记载,这些手稿是鲁迅纪念馆的早期负责人谢旦如先生保存,1962年他去世后,次年他家属捐献给鲁迅纪念馆的。但是,丁玲的手稿怎么会到了谢旦如的手上呢?我们知道谢旦如先生是一个进步人士,曾经收藏了瞿秋白烈士的珍贵手稿,还有中共特派员冯雪峰交给他保管的一些重要文件和资料,包括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但是,谢旦如生前从未谈及这几篇丁玲手稿究竟怎么到了他的手上。按照1980年1月27日丁玲致赵家璧信说的:“我在被捕前,有些稿件、通信、照片,可资留念者,有一个小箱子,或包袱,存在我的朋友王会悟(李达的爱人)那里。我被捕后,即由雪峰、适夷取出来转存在谢旦如家里。”丁玲秘书王增如也回忆说,丁玲曾特意去问过王会悟,自己的手稿怎么会到了谢旦如手上。王会悟告诉丁玲:“1933年你被国民党反动派绑架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更加厉害,我们这些跟共产党来往密切的人都上了‘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抓去坐牢的危险,为了稳妥,冯雪峰把你交给我保存的书信、照片,还有其他材料,都交给了非党进步人士谢旦如,这个人很可靠。”
如此说来,就是王会悟转交的。但其实,丁玲的信和王会悟的说法都不能证明这几篇手稿也在这里面。1982年,谢旦如之子谢庆中提交给丁玲一份捐赠清单,是他们家捐赠给鲁迅纪念馆的文物清单,里面就有这几篇手稿。但严格地说,这仍不能证明它们是王会悟转交的。因为谢家捐赠的物品,还包括冯雪峰从延安带来的《二万五千里》复写稿等显然不是王会悟转交的物品。所以,其中还不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但从情理上分析,仍不排除丁玲手稿是王会悟转交的。因为除了王会悟,丁玲不太可能再交给别人,哪怕是冯雪峰。虽然他们关系密切,他对她帮助极大,她对他极其信任,1936年,丁玲还是在中央特派员冯雪峰的帮助下得以逃离南京的魔窟,奔赴陕北的。在此期间,丁玲在上海的相关事务,都是冯雪峰为之安排的。但是,他是一个职业革命者,生活极不安定,处境比丁玲还危险。特别是,这些物品里包含了她给他的当时她不想也不能公开的信,因此,不太可能加挑一部分出来给冯雪峰。王会悟和李达在上海居住多年,参与了中共一大的筹备。1932年8月,李达转往北平任教。但王会悟和孩子们直到1933年5月丁玲被绑架时还没有动身去北平,也参加了营救丁玲。随后她要离开上海时,把丁玲手稿等转交给冯雪峰,也是很自然的。虽然在直接证据方面还缺口气,但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王会悟交给冯,冯又交谢保管的。
我们知道,谢旦如本人当时家境殷实,父亲是钱庄老板,他是一个所谓“小开”,早年参加“湖畔诗社”,与应修人、冯雪峰关系密切,但与丁玲、王会悟似无关涉。谢旦如保存的很多瞿秋白、方志敏、柔石、冯雪峰、丁玲等的手稿等物品,都是冯雪峰交给他保管的。因为他平时行事低调,貌似与政治无关,不易为人所注意,且为人忠实可靠,深得冯雪峰信任。所以当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瞿秋白紧急转移,冯雪峰会将瞿秋白安排到谢旦如家中避居。所以,冯雪峰把这些重要文件交给他保管,是最可靠的选择。
其次,关于这几篇手稿的署名,也是个谜。这几篇手稿,都署名“丁玲”。这是丁玲最早正式使用这个伴随了她一生的笔名。奇怪的是,在《梦珂》手稿上的署名却是经过反复涂改后重新写的。最初的署名并不是“丁玲”。从手稿上看,最初署名似乎是“迦璘”,有人说是“游璘”,但是被密密匝匝的笔画涂得根本认不出原来的字迹了,然后在下方重新写了“丁玲”两个字。引起热议的是,这两个字的笔迹,与《梦珂》手稿的风格似乎并不一致,因此,有人认为这不是丁玲自己的字迹,就是说:“丁玲”这个笔名是别人帮她起的。而最有可能的,是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
当然这是还可以讨论的。虽然从字体上看,似乎与她平时的书写风格不尽一致,除了“丁”字,“令”字的一捺,也与丁玲的书写习惯明显不同。不排除是由于当时她还没想好究竟用什么署名,边写边反复推敲,以至写了又反复涂抹,然后,当决定用“丁玲”的时候,第一次书写一个连自己都陌生的名字,但又很郑重,所以写得比较工整,跟自己流畅书写的形态有明显区别。其实,“丁玲”这个署名,跟丁玲以后几十年的署名,笔迹风格是基本一致的,区别只在于这个署名笔致比较拘谨,笔迹比较生硬,不像后来的署名那样流畅。“丁”字的一笔一画是分开的,而后来署名往往是连笔的。但这也正常,因为她自己也是第一次用,自然比较生疏。况且之前准备用另一个笔名,涂掉以后,才改用这个署名,在思考斟酌中想定这个署名,也容易导致笔致的生硬。
还有一个证据是:丁玲原稿是用钢笔写的,署名也是钢笔,而编辑用的是毛笔,没必要也不太可能临时特地去找一枝钢笔来代为署名。还可以看到,在署名“丁玲”两个字之间,有毛笔加的一个“<”符号,这是编辑专用符号,表示空一格。这就很明显是编辑所为。这两种笔,就佐证了写“丁玲”二字的是丁玲自己。从种种迹象分析,这个署名应该还是丁玲自己的笔迹。
说到丁玲的笔迹,就会令人想起鲁迅的形容:“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的手稿,鲁迅甚至误认为是沈从文的笔迹。从这几篇手稿看,丁玲的笔迹确乎比较细小、柔润、温婉,富于女性气息。
在手稿形态上,总体上文本修改不多,特别是《梦珂》作为一个青年作者的处女作,其手稿整体面貌的成熟度是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它显示作者构思成熟,思路流畅,我不知道这是一气呵成的第一稿,还是经过反复修改后的誊清稿。虽然写作过程中也有修改,但实在不能说多。按照沈从文的记载:“那个时候,《梦珂》初稿,已常常有一页两页摆在一个小小写字桌上,间或有熟人见到了,问这是谁的文章,打量拿到手中看看时,照例这女作家一句话不说,脸儿红红的,轻轻的喊着‘唉,唉,这可不行’!就把那几张草稿抢去,藏到她自己那个装点信件一类的抽屉里面去了。”(《记胡也频》)沈从文虽然用了“草稿”的提法,但并不能看出是否有反复修改。从手稿上,倒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编者的修改。
从编辑的涂改可以看到,经过他的修改,行文简洁、清晰而且更准确了。比如《梦珂》第一句:“……几个新认识的同学在操坪里打网球”,叶圣陶改为“几个女学生在操坪里打网球”。因为既然是客观描写,没有必要去写是否新认识的。还有些地方,手稿比较潦草,编辑会描得清楚些。比如“没”字,丁玲习惯写法看上去笔画不太清晰,容易与其他字比如“复”的繁体字“復”混淆,编辑就常常给她描得清楚些。还有“窜”字,丁玲原稿写作“躥”,编辑为她很工整地改为“竄”。而且,修改的笔迹,很明显带有编辑的行业特征:笔画清晰,结体端正,容易辨认,是典型的所谓“编辑字”,显然是叶圣陶的笔迹。但还是留下了不少疑问:修改的笔迹,有丁玲自己的笔迹,有叶圣陶的黑色毛笔所改,另外还有一种红色墨水修改的笔迹,也是用钢笔,修改不多,较多是描笔,无法描清则另写,改字的极少。笔迹也很清晰,结体周正,但似与叶圣陶笔迹也不尽相同,因此不敢轻断是谁的笔迹了。然则莫非还有另一人参与处理此稿么?且待更加研究。
最后是编辑技术处理,也颇多未解之谜。稿纸每篇第一页上钤有“小说月报□□号用”的蓝色印章,这不奇怪,是编辑部的用稿印证。但每页上还有一个椭圆形的蓝色印章,印文是“华字部公证图章”,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有华字部、华英字部、西字部、中文校对部、西文校对部等等部门,但“公证”究为何用,却不能很肯定。手稿上还留下编辑标注的排版格式,编辑术语称为“划版样”。排版编辑的字,似乎是另一个人的字,但《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编辑修改更多,因为是日记体,每一天的上方,都标注字号:“五号方头——”。其字体也与另两篇的编辑字一致,这说明,这一篇的批改文字虽然与美编一样用的是红墨水,也有可能是叶圣陶的处理。当然,这些还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这几篇丁玲手稿的意义是多重性的,它们提供了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典型手稿案例:它们完整地记载了一个女作家走上文坛最初几步的完整足迹。从手稿所承载的丰富信息,看到更多丁玲作品的写作过程、写作方式、写作心理和写作状态,以及其面世的过程等等背景情况,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类型性意义与价值的标本。其中的存疑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解开其未解之谜。(王锡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