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人类的命运到底是什么?
江晓原:
《群星》这部小说,表面上是一部以科幻为包装的惊悚探案小说,但小说所采用的背景架构,还是比较宏大的,这正是我欣赏这部小说的主要原因。为了理解这个架构及其意义,我们不得不先从远一点的时代和假说开始。
这事还得从70年前著名物理学家费米(Enrica Fermi)的一句随口之言说起,1950年夏天某日早餐后的闲谈中,费米的几位同事试图说服他相信外星生命的存在,最后费米随口说道:“如果外星文明存在的话,它们早就应该出现了。”由于费米的巨大声望(此时他获诺奖已经十多年了),此话流传开去,被一些人称为“费米佯谬”(Fermi Paradox),竟成为关于外星文明探讨中的纲领性论题。
有了佯谬就会有人来提出各种解释,据斯蒂芬·韦伯(Stephen Webb)的统计,迄今为止已有75种解释。其中相当有影响的一种是约翰·鲍尔(John Ball)1973年提出的“动物园假想(The Zoo Scenario)”。鲍尔认为,宇宙中科学技术持续发展的文明终将取得整个宇宙的掌控权,随后逐渐将落后文明摧毁、制服或同化。他进而假想,地球是一个被先进的地外文明专门留置出来的宇宙动物园。为了确保人类在其中不受干扰地自主发展,先进文明尽量避免和人类接触(他们拥有的技术能力完全能确保这一点),只是在宇宙中默默地注视着人类。所以人类始终未能接触到别的文明——很可能永远接触不到。
小说《群星》采纳了类似“动物园假想”的背景架构,以中国西部名城成都为故事发生地,围绕着“觉醒的人类要不要走出动物园”,人类分成了两派势力,展开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不过,小说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叙事策略,对费米佯缪和“动物园假想”一无所知的读者仍可兴味盎然地读完至少全书前四分之三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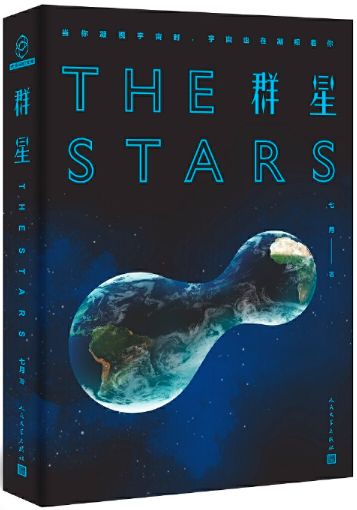
《群星》,七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第一版,45.00元
刘兵:
近几年,我们对谈中科幻小说所占的比例似乎明显有所增加。这次我们谈的《群星》一书,刚出版不久就在科幻圈的一些人中得到了不错的评价。我在阅读此书时,一开始确实也很有些如同你说的那种像“惊悚探案小说”的感觉,尽管是以科幻来包装,或者说是将小说的背景置于科幻的大框架之下。而且,在我们最开始商量选择此书来谈时,你还曾提到,说此书还是很有“阅读快感”的。对此我基本认同,尽管这样的阅读快感与阅读那些更为彻底的惊悚探案小说的快感相比,还略为弱了一些。
此书的主题也是外星文明,外星文明也一直是科幻小说的典型主题。虽然大部分读者并不一定都会很详细地了解费米悖论,不过类似在“动物园假想”的框架中构想外星文明的科幻作品也还是有一些。以你比较专业的研究背景来看,这部《群星》的独特性又在哪里呢?另外,我还有些好奇的是,你说“对费米佯缪和‘动物园假想’一无所知的读者仍可兴味盎然地读完至少全书前四分之三的故事”,这话是算褒还是算贬呢?那剩下的后面四分之一,对于更多的读者来说阅读快感会有所缺失吗?
江晓原:
事实上,进入最后四分之一(只是大致上的,我当然没有统计字数)时,不了解费米佯谬和“动物园假说”的读者,如果他或她一直被探案情节牵着鼻子走的话,确实会感到困扰。例如在铺垫了那么多探案情节之后,读者自然会期待一个谜底的揭晓: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一个科学家和他的一些学生及助手变成了恐怖分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然而,谜底的揭晓,直接依赖于关于费米佯谬和“动物园假说”的知识背景。让我用大白话直接说出来——我所有的书评和影评对于“剧透”从来都毫不介意——是这样的:当人类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在宇宙高级文明设置的“动物园”中时,一派高喊“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主张利用自己的力量走出动物园,而另一派主张先卧薪尝胆,免得高级文明又弄出新的“实验”——其实就是镇压。接受后一派主张的科学家因为得不到人类政府的支持而走上了反政府的恐怖主义道路。
要在上述两派之间站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样的口号确实非常提气,非常鼓舞人心,但是事关全人类的前途,理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人类真的是在宇宙高级文明设置的动物园中,那没有足够的把握,是不是应该先别让高级文明知道“我们已经知道自己在动物园中”呢?先别提“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样的口号,只是悄悄地将它作为我们的信念、我们奋斗的目标,是不是更妥呢?
刘兵:
类似的抉择问题,在《三体》等科幻小说中也都涉及,在《三体》的“黑暗森林”概念中,主动地向外星文明呼唤,几乎等于找死。但似乎有不少科幻作品都是抱着极其热切地要寻找和发现外星文明而不顾其他的心态,甚至许多科学家也是如此。我记得好像你也写过一些文章,谈论一旦真的发现和接触到外星文明可能会带来的风险。
其实在这部小说中,似乎还没有更进一步展开如果真的让更高级的外星文明知道“我们已经知道自己在动物园中”之后可能会给地球人类带来的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后果,而只是局限在故事里有限人物对此的不同态度和选择。就像众多科幻总在关心人类向外太空移民,但对地球自身的关心却远远不够,更少考虑在现实中能够移民的人数与地球上更多人类不可能移民的平等和公正问题。这也涉及我们以往所谓的谈论科学的目标和相应地认识“真理”“真相”的立场和态度。就像在另一些场合人们争论的科学研究是否应有禁区一样。
在这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人物对话:“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系统里是没人有办法把它叫停的。这就是构造体的可怕之处,就像毒品一样,不管你是否明白它会毁了你,你自己都是不可能戒掉的。”“这东西就是为我们设计的毒品。人类最大的优点在它面前也就是最大的漏洞。”延伸一下,在那种为了探索所谓“真相”可以不顾人类命运的立场背后,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是某种这样的“毒瘾”呢?
江晓原:
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理解。这又回到“要不要主动寻求与外星文明的接触”这个老问题了,在欧美,至少到20世纪下半叶,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相当热烈,两派的立场明显对立,各自陈述过不少理由。
反对主动接触外星文明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外星文明会对地球上的人类呈现恶意,会对我们进行掠夺和征服。史蒂芬·霍金在前几年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站队表态时,也明确表示人类不应该主动寻求与外星文明的接触。《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概念也是同样的意思。
那些不顾一切要主动与外星文明接触的人则认为:凭什么断定外星文明一定会对地球人类表现出恶意?说不定他们很友好呢?说不定他们还会愿意和我们分享自己的科学技术知识呢?哪怕只分享给我们一点点,说不定人类文明就会有突飞猛进的进步呢?
但是,已有的证据明显有利于霍金和《三体》的主张。证据很简单:外星文明对地球人类表现出善意的例证,迄今为止是零。虽然由于人类迄今为止还未曾和外星文明接触过,所以外星文明对地球人类呈现恶意的例证也是零,但我们毕竟已经有可以参照的同类例证:当年欧洲殖民者是如何对待玛雅文明的?美国人又是如何对待印第安人的?玛雅文明和印第安人不就是落后文明遭遇先进文明时的命运吗?所以现代的西方学者只要回忆一下自己祖先对落后文明的所作所为,就不难推断出,先进的外星文明如果在“黑暗森林”中发现了比他们弱小落后的地球文明,会干出什么事来。
回到《群星》中的“动物园假说”中来,能够设置“地球动物园”的文明,肯定是一个远比地球人类发达的外星文明,作为动物园的“管理当局”,这个外星文明对地球人类会展现出恶意还是善意呢?小说里没有给出答案。
让我们再次用唯一的样本——我们人类自己——来推测一下吧:我们平时当然会保护珍稀动物,甚至鼓吹动物保护主义,但是,如果,我们动物园中的动物们“觉醒”了,它们大义凛然地喊出了“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作为征途的第一步,比如说,它们要接管动物园所在的城市,那等待着它们的会是什么?当然只能是无情的镇压。
刘兵:
我们已经从《群星》的具体情节延伸到其背后的费米佯谬、“动物园假说”以及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了。如果我们真是生活在一个被外星文明设置的“动物园”中(这倒也与《黑客帝国》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参照人类自身不同等级文明相遇的历史(当然这还是以地球人来类比外星人),地球文明面临的威胁是不可忽视的。
但仍然有人热衷于寻找外星文明,在这背后似乎有一种思维方式和立场在起作用。就在我们对谈《群星》的这几天,中国大地上正面临着新型肺炎的疫情危机,对此,至少人们的一个共识是,不要去招惹野生动物,我们自己守着自己的领地好好生活就是了。但在类比中,那些积极要探索外星文明的人,在思维方式上,不是与积极探索、征服(吃掉)野生动物的做法也颇有相似之处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说“好奇害死猫”,在对外星文明的探索中也许就会变成“好奇害死地球人”。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样的看似非常保守的观点,又会与积极探索未知的“科学精神”相矛盾啊!
江晓原:
你的联想确实不无道理。比如,在小说近结尾处,汪海成和白泓羽的对话中,汪主张先卧薪尝胆,继续发展地球文明,可以说很有人文主义色彩;白主张勇敢地走出去,奔向星辰大海,思路明显是科学主义的。科学主义喜欢在“寻求真相”“追求真理”“奔向星辰大海”之类看似大义凛然的口号下,不顾一切地追求某种技术性的短期目标,却将人类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置之脑后,这实际上是忘记了搞科学研究的初心——搞科学研究的初心应该是增进人类的福祉,而不是为了“发展科学”而发展科学。
其实我不反对“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样的口号,事实上我非常喜欢这个口号,我坚信终有一天我们会奔向星辰大海。但在这个征途中,我们一刻也不能离开理性思考。
刘兵:
那我就唱一句反调吧:当心中存着“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的信念时,就很难做到在征途中“一刻也不能离开理性思考”。当我们总是讲科学与人文要结合时,其实总是很难在现实中将两者真正同时兼顾。而且,在科学愈发强大的现实面前,更多的人总会将科学置于更优先的考虑。但我们毕竟是人类,在这个意义上,我宁愿更强调人文优先!
(江晓原为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刘兵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本文为中华读书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策划的“南腔北调”对谈系列第17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