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奇到世情:文学中对上海的新想象
在文艺作品里,从来就不缺少与上海有关的刻板印象。比方说,只要在影视剧中有上海男人登场,则八成是个妻管严加胆小怕事的形象。要是有上海丈母娘登场,则大概率呈现出的是拜金加挑剔的嘴脸。
这当然不只是一个“地域炮”的问题,毋宁说,这一现象和文艺领域,尤其是文学中的上海想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什么是上海?毋庸置疑,它可能是茅盾笔下的商业,可能是张爱玲笔下的人性,也可能是王安忆笔下的欲望。似乎,受众心目中的上海形象,不过是在以上几种模型之间来回切换。
就在今年11月,泽东电影公司官方微博晒出来一张《繁花》的概念海报。虽然退到了监制的位置上,但王家卫和金宇澄的强强联手,仍然值得期待。而我最为关注的是,《繁花》能不能改变一下上海这座城市自带的刻板印象?

电影《繁花》海报
如果说茅盾书写的是上海的“史诗”,那么张爱玲与王安忆描写的则是上海的“传奇”。她们作品中的奇女子代替了革命的斗争,占据了文学舞台的C位,也几乎成为了文学上海的代名词。只是,弄堂、旗袍、石库门……这些“传奇”里的必备品,却渐渐沦为一种新的文学套路。然而,横空出世的《繁花》,试图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写出真正鲜活的“世情”,对抗固化在读者脑海中的上海“传奇”。
在 《繁花》尾程,一次酒宴欢场,“夜东京”的女老板玲子,从那一桌来这一桌搬救兵,要叫上她的小姐妹小琴去跟陆总喝酒,小琴的现任相好陶陶不让去。此时,玲子说,“陶陶认得小琴,也就是这种胡天野地场面嘛,不要忘记,是我摆的场子,现在一本正经,像真的一样。”另一边,陶陶“不响”。
如果说,张爱玲与王安忆笔下的女子尚有对纯真情感的渴望,只是因为人性的扭曲或世俗的误会而未能如愿,那么这场饭局,无疑彻底击碎了一切幻想的可能。“一本正经”“像真的一样”,但毕竟不是真的。从小说的情节来看,陶陶、小琴之间的感情果然如玲子所言,建立在海市蜃楼之中。
但更重要的是,这两人从来就是以自身为目的,以他者为手段。即便是陶陶的“当真”,终究也只是一种错觉。换言之,就连张爱玲小说主人公求而不得的目标,也是不存在的。去除浪漫、回归生活,这正是金宇澄的“世情”与张爱玲的“传奇”最根本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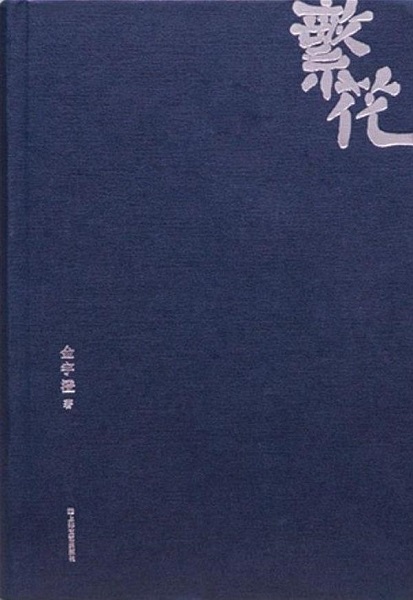
《繁花》
有意思的是,这一有关上海的文学创作转向,不仅仅出现在了金宇澄的作品里。吴亮的《朝霞》,是一部反叙事、反主题、反人物的“反小说”。或许正因为作者太熟悉小说创作,所以更要在创作中率先进行自我“批评”,自行排除一切“套路”。但在这部看似纷繁复杂的作品里,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世情”而非“传奇”的存在。
《朝霞》中,生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阿诺以及他的朋友、同学常常谈论政治,然而“这种不再读书阳光灿烂的日子,在他们看来简直糟透了,他们疏离政治,他们论政治不是为了好奇,而是政治影响他们的命运和未来,倒不是对这个国家有多少关心”。这实在是一种悖论——他们关心政治,可又主动疏离于政治。
这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19世纪俄罗斯小说中常常出现的“多余人”。只是,“多余人”并不缺乏高昂的理想主义,他们的受挫或失败往往来自于社会的重压。然而,《朝霞》中的年轻人们时常“请病假消极怠工,抽烟并且过早地谈情说爱,不务正业且 ‘游手好闲’”。换言之,他们从来没有挑战社会、挑战世界的想法,更不用说行动了。
在阅读过程中思考、怀疑甚至踩踏思想的禁区,却无意挑战或反抗,这正是《朝霞》“反传奇”的最生动体现。这群年轻人不是令人惋惜的悲剧英雄,也不是毫无头脑的市井无赖,他们只是他们自己,他们代表的就是“世情”,是一个活生生的特殊时代的上海。
张怡微对上海“世情”的探索,同样不该被遗忘。在她的《细民盛宴》里,描写了主人公“我”与小茂的一段短暂、仓促的婚姻。在这桩婚姻里,父亲执意要“我”相信,没有给嫁妆并不是不爱女儿;“我”与小茂父母初见的宴会上,小茂父母便直接、赤裸地评估“我”以及“我”的家庭收入到底是否能承受得了双方的爱情。
对张爱玲来说,“算计”是现代大都市中的人性之恶,是摧残爱情、善良的根源。但张怡微给予了这种“算计”更多同情和理解。因为在她看来,生活在上海,面对着局促、逼仄的现实,人们或许只能依靠精确的数字来获取一丝岌岌可危的安全感。和跌宕起伏的“传奇”相比,这才是当代上海的“世情”。
正如张怡微所言,“只要说到上海,人们想起的都是旗袍、背头、老洋房、石库门,但这些意象我都很不熟悉,我也是看来的”。因此,怎样把“传奇”之外的上海生活纳入文学,也许是更多写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密林中》
周嘉宁正是这么做的。她的《密林中》,叙述了恋爱、成长、迷茫这些经常出现在青春文学中的要素,却也不缺少一位年轻写作者的文学的自我意识和野心。小说主人公阳阳在历经沧桑后,既没有获得写作事业上的真正突破,也没有放弃探索和努力。或许,这才是生活的常态,而不是“传奇”的面貌。
在她的笔下,上海成为了“密林”。阳阳看到的,是生活方式的空洞、无趣,是生活背面的疲惫、空白。阳阳“灵魂的作坊”受困于“密林中”,而“密林中”的困境经验不是别的,正是无穷无尽的“世情”。
另一位年轻写作者走到了她的对立面,那就是郭敬明。在他的作品中,上海异化为“资本”和“时尚”的代名词。可尽管如此,“小时代”仍然精准地命名了某种真实存在的“世情”,那就是一部分年轻人无所顾忌地向金钱、向权力献媚的姿态。
有车有房、名校名企、英俊爱人、充满“时尚”的中产阶层生活,或许都是“世情”的一部分,但注定是倾斜、偏颇的。因此,郭敬明努力描写的大都会“传奇”必然与历史脱钩,带来的则是读者心理上的悬空之感。何况,与张爱玲、王安忆对人性的洞察相比,他笔下的人物近乎抽象符号。
因此,克服郭敬明式虚伪观察的关键,仍然在如何准确地把握、书写上海的“世情”。就此而言,任晓雯的《阳台上》无疑是个值得关注的例子。小说以张英雄的复仇为主线,描写的是上海底层社会空间的时代变迁。
在2019年,被改编成电影的《阳台上》里,出现了一段原作中没有的情节——当主人公张英雄为庆祝自己的生日第一次许愿说“我希望国家富强、世界和平”时,被父亲掴了一巴掌说 :“为自己!”这一幕体现出的是张英雄自我认知、自我认同的困境,却也是上海普通家庭所身处的“世情”的真实写照。张爱玲的“传奇”远离了茅盾笔下的宏大说辞,但绝不缺乏“意义”“主题”“理想”。可在张英雄看来,生活就是“有房、有退休金、有老婆、有孩子,没事可以咪咪老酒。”既不伟大,也不虚无,对上海的文学描写,就这样落到了实实在在的“世情”里。
在《繁花》结尾,有意来拍摄电影的法国青年满脑子上海传奇,阿宝们却不断提醒其苏州河畔并无法国厂。法国青年安排男女主角在装满棉花的驳船里做爱,阿宝却说当时的棉花船上都养着狗,避过恶狗耳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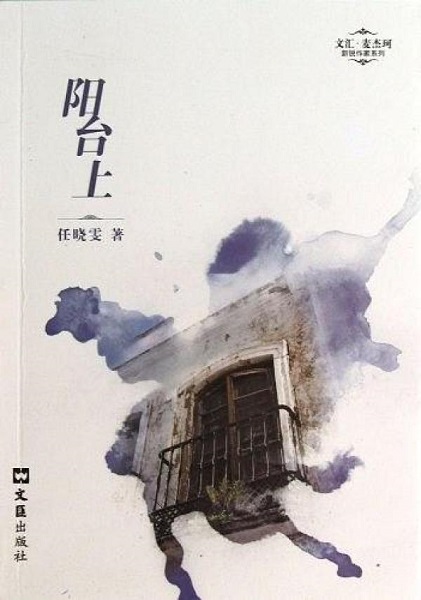
《阳台上》
这段情节隐喻的显然是对上海的认识。“传奇”对上海的描摹,就和法国青年的浪漫幻想一样,很诱人,很动人,却和真实的上海相距甚远,充满隔膜。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在书写上海时,正在努力突破“传奇”的束缚和套路,这绝不是偶然现象。
只是,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上海?谁有资格制定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这些问题,注定不会得到一个百分百正确的答案。但写作者的尝试,绝非没有意义。归根到底,从“传奇”到“世情”,对上海的文学想象模式正在潜移默化中被颠覆。它的新生,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