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我从未怀疑过真善美

这位与共和国同龄、因知青文学而蜚声文坛的知名作家,在过去四十余年里,留下《雪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风靡大江南北的作品。教师、作家、政协委员,在耀眼的光芒中,梁晓声真实而恳切地表达着自己的声音,至今,他创作了1000多万字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杂文以及影视作品。
2017年,他推出三卷本《人世间》,2019年推出《梁晓声童话》。两年来,他的童话系列不断丰富、拓展,建构着充满真善美的童话世界,并向这个世界传递他对儿童成长深切的爱意、体贴和关怀。
“我早该从儿童文学中拔腿而出了。”三四个月前,梁晓声对笔者如此说道。可是他无法潇洒地转身就走。因为他在这个领域仍有不断的思考和想要表达的欲望,新作《我那些成长的烦恼》是梁晓声为少年读者创作的一部自传体成长小说,讲述他从儿童到少年“成长的烦恼”,底色依然乐观而光明,叙述苦难却不失温暖甚至幽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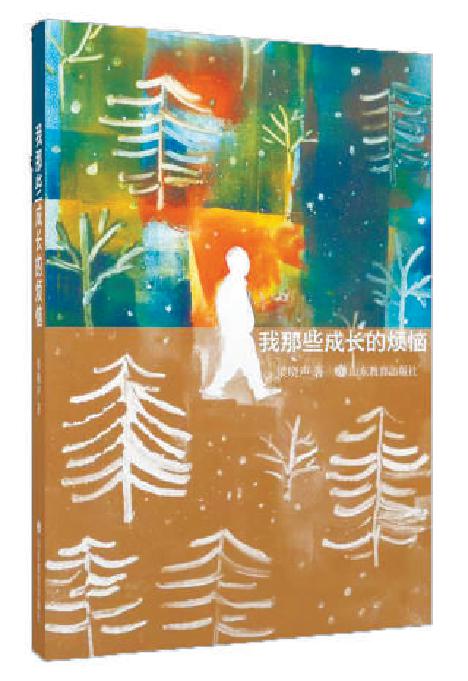
1 教化爱永远都不过分
之所以写童书,梁晓声自有原因:一是他的成长史中没有童书阅读经历,小时候没那么多童书,家里也没有钱买。他是成为作家之后读了一些童话,包括很多以儿童视角切入的温暖的、带有童话色彩的成人作品,对他的成长影响特别大。他想,自己是作家,应该写这样的作品;二是梁晓声在儿童电影制片厂十多年,长期关注儿童文学,他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国外的动画中动物和生活联系在一起,比如《帕丁顿熊》,熊和形形色色的大人的成长连在一起。国内的儿童文学不是这样。父母带孩子进电影院,什么最逗乐看什么,因此我们看贺岁片,有一个共性就是“乐”字。
梁晓声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让母亲和孩子一个乐子接一个乐子。可是一个声音明确地告诉他:不能写。
“不能读者想要什么写什么,我只写我希望你们读的东西。”梁晓声说,他有意识地希望孩子看一看,故事该怎么讲。万一孩子读了以后作文有进步了呢?万一影响谁成为作家了呢?万一对孩子的性格养成有好的影响呢?“我给自己规定了要做的事情。如果你是评论家,你会发表倡导的评论言语,希望童书怎么样;我是作家,就要拾遗补缺。”
他发现,童书在很大程度上有两点是要补充的。一是励志。很多童书主题跟《狮子王》差不多:“我行,我一定行!”像安徒生的《丑小鸭》,它是天鹅种,如果它是野鸭种呢?所有孩子不可能都是“狮子王”,不可能都是海鸥乔纳森。理发师、面点师……平凡的人就不能出色吗?梁晓声的《白鸭阿甲》便是传达“平凡也能出色”的观念。再就是爱心。现实生活中缺失爱心的例子不少,比如动物被虐待,比如一只为家庭下了那么多蛋的母鸡,外国文学中都会成为人类的朋友,但是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不是。这是梁晓声要通过《“白先生”与“黑勇士”》传达的。他觉得,爱心要从娃娃抓起。现在社会竞争如此激烈,严重到小学生会连复习提纲都不愿意借给同学看。《蕾蕾和姗姗》就描写了竞争状态下的友谊。
“我不太知道是不是所有家长都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能赢,要么自己言传身教,要么借助读物来给自己的儿女找到一种力量,好像恨不得尽早让孩子明白:这是一个竞争的世界。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这样的话,家长和拳击教练有什么区别?如果只能恶而强,我们的文化岂不是地球上最奇怪的?为什么不想我们有可能善而强?”不能否认,梁晓声确实有主观创作的意图,就是传递友谊。首先你要有感觉。别人对你的友善,你没有感觉的话几乎等于不存在。一个人抱怨生活不如内省自己。如果抱怨别人冷,是否别人给你温暖而你没有反应。他提醒读者感激友谊,哪怕是微小的帮助。
同时,梁晓声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童书未必都是受欢迎的。也许有些母亲会说:“我的孩子凭什么让你教育?”可是即使受到某些母亲的心理排斥,他也拿定主意写。哪怕被贴上“教化”的标签。他认为,教化爱永远都不过分。全世界、全人类千百年来都一直重视对儿童的教化。“教化”二字一定是庄重的。
2 对现实主义充满敬意
梁晓声的现实主义题材写作一以贯之。《人世间》(三卷本)全书115万字,从20世纪70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以北方省会城市一位周姓平民子弟的生活轨迹为线索,刻画了十多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堪称“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学记录。
与梁晓声此前的知青文学题材的作品相比,《人世间》中不乏北大荒知青岁月的片断,但是笔墨更为开阔,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抒写情怀和热望,由小见大地窥测出大时代的匆匆踪影。
梁晓声表示,自己一直对现实主义深怀敬意。因为他在文学少年和文学青年的时候所看的长篇小说大部分是现实题材。“下乡”前他看了相当多的外国文学,很多都有现实主义品质。到了上世纪80年代,基本上还是以现实主义题材为主,老中青作家都在秉持现实主义精神。但是200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文学中的现实题材少了,尤其是有年代感的现实题材少了。
“我写《人世间》,也有向现实主义致敬、向新时期文学致敬的夙愿。”梁晓声分析,优秀的现实题材缺少的原因,是一些作家有畏难情绪,而他的性格是愿意知难而上。还有一个隐秘的情愫:他对当年的“大三线”建筑工人心怀敬意,希望用作品为他们画一幅肖像。“我父亲是‘大三线’建筑工人,他几乎走遍了大西北各个地方。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多子女的家庭可以有一位子女留城。因为学历低,留城的子女从事的多是城市低端的体力劳动,而且心灵孤寂。底层人家的父母辈,多是沉默寡言,而且很严厉,小儿女们不会跟父辈交流,如果没有书信,也没法和哥哥姐姐们交流。这种孤寂中成长的小儿女从来没有被人关心过,文学画廊里这样的人物不多,我愿意为他们画一组素描。”
《人世间》写完之后,梁晓声有很长时间缓不过劲儿来。作品上部是用行楷写,还比较工整,到了中下部的时候,字体就变了,写完全部作品后,他已经拿不动钢笔在方格纸上写稿子了,开始用上了铅笔和A4纸。《人世间》下部还没写完时,梁晓声一度感觉非常不好,就到北医三院化验科做检查。
做过化验后,梁晓声就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北医三院电话通知他到医院取片子时他竟以为是骗子。医生告诉梁晓声,情况很不好,建议做第二次胃镜,三个月以后手术。实际不到三个月,梁晓声就转到肿瘤医院,医生和他商量动手术,希望做全部切除。胃癌治疗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有家族史(梁晓声的父亲就是晚期胃癌),选择胃癌前期全部切除,防止扩散;也有另一种可能,五年十年没有发展。
梁晓声想,自己的书还没写完,胃如果切除,意味一切都要停下。离开肿瘤医院的路上,他吸了两支烟。扔掉烟蒂,他拿定了主意:相信自己的抵抗力,选择保守治疗。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不但完成了《人世间》,2021年1月,梁晓声在获得茅奖后又拿出了新长篇《我和我的命》。书中,梁晓声通过主人公之口,表达了很多对社会、命运和“活着”的看法。小说里讲,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人的总和显然与这三命有密切的关系。梁晓声在小说中对“命运”倾注了最深切的关怀。他写出了命运之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也写出了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生活依然复杂,生命依然昂扬,奋斗依然坚韧,小说冷静看待“命运”,既相信命运、热爱命运,又努力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和。
他在书写知青生活、社会阶层变化的同时,思考着社会对人的要求、时代对人的改变、困难对人的考验,同时也在呈现人对这些要求、改变和考验的回应。《我和我的命》中,人物的回应更多地内化为一种责任和修养,承担起生命、家庭、社会带给人的责任。
这部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女性成长话题。作家用几位女性的命运,不断发问:你相信奋斗能够改变命运吗?个人奋斗到底是为了成功,还是为了每天都过得充实?大千世界中,漂泊人世间,我们该怎么安放自己,才叫与命运和解?如果注定一生平凡,我们该怎么办?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梁晓声(右二)与其他获奖者。
3 文学的意义
“父亲目不识丁。祖父也目不识丁。”梁晓声在自传体散文《似梦人生》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母亲也是文盲。外祖父读过几年私塾,是东北某农村解放前农民称为‘识文断字’的人。”后来,北大荒的知青经历,及至1977年,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梁晓声的命运彻底改变。
2002年,梁晓声调到北京语言大学。在此之前,梁晓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儿童电影制片厂,始终“在场上”。但到大学讲文学课,他首先面对的是回到文学的意义。
以前他几乎没有想过何谓文学的意义,甚至也不知道从哪个角度讲起。后来他想起来,法国雕塑家罗丹有一个著名的雕像“人马”。这个希腊神话中的怪兽,对人和神都会形成共同的危害,它有人的上半身,上半身拼命向上伸展、扭动,那种动感分明体现它要从马腹中挣脱,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只有双足落地,才能成为大写的人。
梁晓声突然悟到:文化所化的过程就是从马的躯体挣脱出来一个完整的人,这是一次脱胎换骨。从那时起,他调整了自己的创作理念。
古今中外之文学现象,大抵可归为三类:一类以揭示人之“人马”真相为目的;一类以呈现人如何努力成人为要义;一类昭示人之为人之后的善好,并且证明这是人皆可以实现之事。
梁晓声不属于第一类作家,因为那创作过程首先便不合自己的心性;他也不属于第三类作家,因为在他所感受的现实中,“大写”的人、“纯粹”的人不是没有,委实甚少。并且,他对于何谓“纯粹”的人,目前也还未得要领。于是,梁晓声的创作逐渐形成符合自己心性的理念,即呈现人不但要一心成为人,还想一心成为好人的过程。梁晓声的观念是,文学本身是文化的副产品,又应该是文化的长子。假如是长子的话,生活中的长子,都要替家庭承担一些责任,文化的长子看到了文化在那里发挥作用发挥得那么沉重,也要做些什么,“我是把文学创作放在文化背景上,而不仅仅是文坛上。这样的意义才符合我的理念。”
在北京语言大学期间,每年开学面对新生,梁晓声都要花很长时间调查、了解学生的个人愿望是什么,在评论还是在创作;还要不厌其烦地告诉学生们学习中文的意义。他要求学生首先清楚中文系学生的基本能力是什么,这种能力对迈出校门后的职业选择有什么帮助。然后他会根据学生不同的兴趣引导他们。他认为,中文系学生的能力有三个标准:一是评论的能力;二是研究的能力;三是创作的能力,最后这个能力比较特殊,需要考核是否具有潜质。他这样要求学生,其实自己也在身体力行,他还常常在课堂上点评学生的作品,支持他们办刊物。多年以后,学生们大概还会记得梁老师课堂上孜孜不倦的教导:情节像天使,细节像魔鬼。天使差不多都是洁白的羽毛,细节却不一样,每一个细节都会在学生心里打上深深的烙印。
他的案头摆放的不止是自己的作品,他随身携带的白色布书包里,常常装着学生的论文、习作及他自己的讲稿。既不按照别人的教材讲,也不准备重复的教材。他每一堂课的讲稿,都要有七八页纸。“我的每一堂课都是结合上一堂课,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写教材。讲得用心不用心,备课或不备课,学生一听就能听出来。”虽然对于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什么尚属未知,但是他依然执着地坚守自己的原则。当老师是他少年时期的梦想,他愿意为此全力以赴。
4 不要一味批判,也要给予
最初从事创作时,梁晓声非常崇尚鲁迅。我们强调鲁迅的投枪匕首,其实就是社会批判的功能。这种社会批判的功能几乎成为一代人认为的文艺最光荣的功能。但事实上在创作实践中,整个批判不能深入下去,于是投枪和匕首成为一种情结。
诚如巴尔扎克所说,小说是民族的秘史。文学应该是室外之室,历史没有细节,文学中有毛茸茸的细节,文学工作者是时代的书记员。在梁晓声看来,这个观点和仅仅持鲁迅的投枪匕首观点不同,书记员不仅把握文学批判唯一的功能,还要记录真善美,记录生活稳定的价值观,即使在特殊年代也不放弃的固守。了解到这一点,梁晓声便要求自己在作品中不要一味批判,也要给予,变成蝙蝠和蜜蜂。蝙蝠意味着不祥,本身有着警示的象征,蜜蜂却要酿蜜,这两者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作为作家,他希望这两方面的文艺功能都要实践,而且要实践得好一些。
梁晓声常常反思:中国社会生活和文艺的关系,理解少了,包容少了,温暖少了,互相贴近的愿望少了,对于善良的那种相信,也少了。生活中有这么好的人么?当我们不断这么疑问时,问过多次,约等于生活中没有好人。当我们不断通过文艺作品来认知,生活如此险恶,最后得出结论,生活就是这么险恶,如果是一个哲学命题,最后在文艺作品中成为母题暗示。假如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艺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对于国家和民族是悲哀的。
回顾多年的创作,梁晓声有两点总结:“凡是我的哪部作品好一点,都由于我在创作中没考虑到市场、稿费、印数、改编成影视收入多少,我只是相对真诚地把我的感受呈现出来;凡是我的作品中我个人觉得不好的、失败的,都是由于后一些因素进入了我的创作意识。有时候有些因素会产生诱惑。”他说,一路写来,对于写作所剩时间不多,要把自己摆放在文学、文艺、文化和整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的关系中。在这个关系中,他考虑最多的是,怎样写才能更对得起创作了几十年的作家身份。
在他看来,文学作品之所以高于生活,不是把生活粉饰之后高于生活,而是把人性的真善美所能达到的高度呈现出来,文学高于生活最终是高在这里。只是这样的作品需要用眼、用心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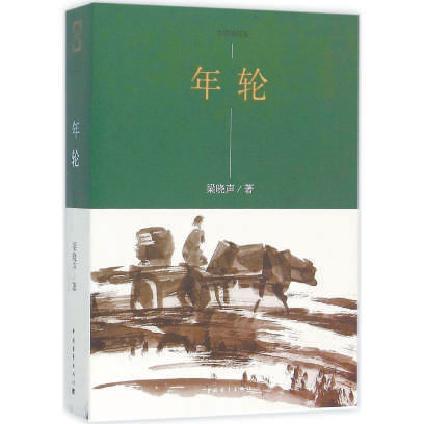

尾声
他似乎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时代的变迁、周围的喧嚣,几乎没对他形成任何干扰。无论什么时候见面,他都真诚地称呼:“亲爱的同志……”这亲切而遥远的称呼,从梁晓声口中说出来,妥帖又温暖。
堪称中国文坛常青树的他一路写来,几乎所有作品都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始终秉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和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关注一直是他创作的初心。他也一直在积极倡导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人世间》,就是一部关于苦难、奋斗、担当、正直和温情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通过一个个可亲可感的人物全景展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关于文化,他曾经有过四句广为流传的表达:“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这样的价值理念也始终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