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开距离说“晚熟”
今年8月,莫言终于出版了自己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八年后的首部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尽管出版一部新著对过去的莫言而言无异于一件“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常事,但他这次的出版行为却必将酿成一桩 “事件”。何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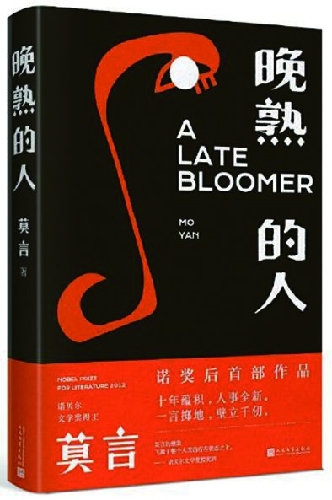
《晚熟的人》 莫言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莫言的创作力毋庸置疑,莫言的创作量虽算不上最高,但也绝不至于低到八年才出版一部作品,况且还只是一部中短篇小说的结集。莫言这是怎么啦?难道莫言也患上“诺奖后综合征”?单是这两个问号就足以具有强大的“吸睛”力,而一旦形成强大的“吸睛”力,自然也就成了一桩“事件”。果不其然,《晚熟的人》甫一面世,立即形成文坛乃至社会热点话题之一。现在三个月过去了,关于“晚熟”的热已然降温,拉开了这段距离再来回望“晚熟热”和《晚熟的人》作品本身,或许也是一种“晚熟”。
《晚熟的人》的确有不同于一般作品之处,它足以从不同的维度去观察、去考量,从而触发不同的话题:
——比如从市场反应角度。《晚熟的人》上市不足三个月,销量直逼60万。必须要点透这个60万背后的不易:第一,这只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在中国的文学图书市场上,新小说集的销量普遍远不及一部新长篇小说新作的销量,而在当下市场中,一部新长篇的首发能在两万册左右就已是不错的业绩;两个月直逼60万册的销量即便是整个文学图书市场的排行进入TOP10应该不是问题;第二,尽管今年8月到11月我们已进入“后疫情时期”,图书市场开始缓慢复苏,但所谓“报复性”消费并未在这里出现,实体店尽管有两位数增长,但那终究只是以上半年的业绩为基数;线上渠道看上去热闹,但终究也只有三五个点的增幅;第三,依照前三个月的销售态势或过往的行业经验,60万册的销售绝对还远未触顶,高位在哪不好说,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晚熟的人》将会由畅销转为常销。仅此三点,绝对就足以称其为当下中国文学图书市场上的一个典型案例。
——比如从话语流行角度。《晚熟的人》中的“晚熟”二字迅速成为一个可以从诸如人生、处世、反讽、自嘲……等各个角度进行解读的社会流行语,一时间“晚熟”成为人们交流时的一种谈资。这种现象令人想起本世纪初中信版的引进图书《谁动了我的奶酪》和《邮差弗雷德》,书名中的“奶酪”随即成为 “如何面对改变”的隐喻,而 “邮差”则一度成为忠诚、敬业的代名词。这种现象很有意思,背后所折射的其实是彼时彼处社会比较普遍存在的某种精神、情绪或心理状态。在一定意义上,这或许也是莫言的这部新作迅速热销的缘由之一呢。
当然,这些个角度固然和《晚熟的人》皆有关联,但基本上又都还是游离于作品的边缘。至于《晚熟的人》是否真的意味着莫言创作的“熟”,那还得深入文本本身考察后再下判断,而且我相信这种判断依旧难免众说纷纭。
其实,在莫言这样层级的作家的不同作品之间硬要分出个伯仲叔季,本身就是一种“自取其辱”的行为。本文标题说的“晚熟”绝对不是说莫言在获得诺奖八年后的创作更加成熟,而是指较之于他此前的创作,《晚熟的人》中的艺术表现的确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我注意到这部集子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整部作品集收中短篇小说凡12篇,其中最早的一篇创作于2011年;三篇起稿于2012年,但直到2017年才改定;四篇创作于2017年,四篇即创作于今年。在这12篇中,越是创作时间靠后者,其变化的痕迹就越明显。
这些个变化在《晚熟的人》上市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先后已为那些睿智的读者们一一指出。要感谢当下这个伟大的“互联网”时代,借助于强大的搜索引擎,我们可以很便捷地转引罗列几则有趣而又有事实支撑的说法:
比如:打滑的文风不再明显,溜冰看不到了;
比如:依然是取自故乡人事,但奇人异人少了,更多的是聚焦当下,融入自己对社会新生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比如:不再聚焦英雄好汉王八蛋,而是转向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人物;
比如:过往那种汪洋姿肆、梦幻传奇的东西少了,更多了些冷静直白、静观自嘲;
比如:12部作品中的11部都有一个老莫言之外的新莫言出现;
…………
以上描述的这些变化虽未必完全确切,但大体也都是客观存在。何以要“变”?固然可以从求新求变是文学创作永恒的追求这个角度来解释,但如果我们将莫言的这些变化置于更长的时间和更广的空间予以考察,或许又会有另一番心得。
莫言的处女作虽发表于1981年,但其成名却要到四年后《透明的红萝卜》面世,特别是再往后一年《红高粱》在《人民文学》杂志的刊出,莫言这两个汉字在新时期文坛留下的深厚烙印就再也无从抹去。那毫无羁绊的奇特想象、对色彩的奢侈泼洒、对通感横冲直撞的调度以及恣意纵横的叙述都使得看惯了传统文学作品的文坛为之一惊:红萝卜咋就透明了呢?抗战居然还可以这样表现……其实就在莫言名声大振的同时,还有一股力量也在迅速崛起,那就是被称为“先锋文学”的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马原等一批青年作家的迅速崛起,他们的创作固然各有其特点,但其共同的“先锋”称号又昭示着他们创作的一个相同点——实验性。莫言与这批“先锋”作家同时同场亮相,但同样充满实验性写作的莫言却从未归于“先锋”的大旗之下,这也是我心中的一个未解之谜。难道就仅仅只是因为莫言稍稍年长一点,还是莫言的实验表面上没有那几位作家走得极端?这些似乎都是题外话了,但不管怎样,莫言也好,先锋作家也罢,无论他们间的创作呈现出多大的差异,但其文学创作的血脉中都流淌着一支共同的血型则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自19世纪末兴起至20世纪上半叶走向极盛的虽名目繁多但却被统称为“西方现代派”的文学。
站在今天来回望上世纪80年代后半叶的这段文学发展历史,无论如何评价,本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我们总得承认这股文学思潮在那时的出现一定有着当时社会的、时代的、文学的等多重原因综合使然。而如果我们将视野进一步放大、视线进一步拉长,我们同样又会发现:世界上的许多文学创新的始作俑者一开始常常都是以极端甚至偏激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追随者则或多或少地带有生涩的痕迹。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些极端的文学方式渐呈司空见惯之势后,那些个创作上曾经走过的 “极端”便随之开始 “反拨”,当然这些个 “反拨”绝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在新层面上的一次新的融合。考察上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学以及新世纪的中国文学,都能够清晰地看到这样一种发展变化的轨迹。
离开《晚熟的人》而极为简略概括地回溯了刚刚过去不久的这段历史,其实就是想为莫言何以“晚熟”提供一个更宽的视野和更长的视线。置于这样一个稍大些的时空中再来看莫言的新作,变化显而易见。不仅莫言在变,余华、格非、苏童……后来的写作不也同样在发生变化吗?而仅就莫言的“晚熟”而言,给当下文学创作带来的思考也是多维度的,比如对深刻性与可读性关系的处理,比如对叙述主体的“复调”式的使用,比如明写实暗反讽的鲜明对比等等,只是限于篇幅就无法一一展开了。
一句话:我想在获得诺奖八年后,莫言如果依旧不见新作,或是推出的首部新作依旧“一如既往”,那就不是“晚熟”而是“夹生”或“熟大了”呢。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