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中秋词的人生突围与艺术超越
在中国传统节日中,中秋节的地位非比寻常,它不仅被寄托了团圆和美等诸多美好情感,更是文艺创生的土壤,催生了数不清的经典作品。就词而言,历代咏中秋的佳词并不鲜见,但格高千古、空前绝后的非苏轼《水调歌头》莫属。恰如宋人胡仔所云:“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明人杨慎也赞其为“古今绝唱。”(《草堂诗余》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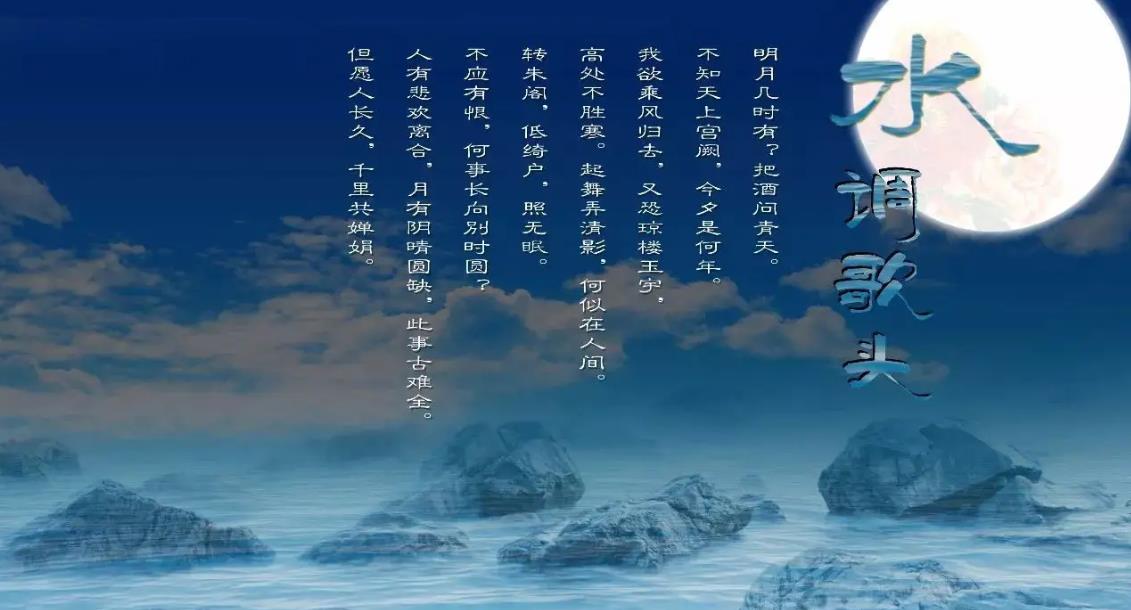
对这首经典作品,人们从创作主旨、艺术风格等角度切入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如果只是重复前人的老调,即便有一二新意,意义也不大。但经典作品的价值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或后人的阐释而削减,对不同的时代来说,经典作品永远都是“新”的。立足于当下的话语体系,透过作品文本的显在结构,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雾,直抵作者的心灵深处,进而感悟宇宙社会人生的常道,必将有新的体验和收获。
在诗词的解读与赏析中,不应拘于文本但也不能脱离文本。《水调歌头》一词有苏轼的自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小序不足二十字,却是我们解读词作的钥匙。丙辰年,即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苏轼调任密州的第三年,任期将满,可是前途仍然黯淡不明。纵然“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却无由施展。七年前,苏轼兄弟服孝期满后由故乡返回京师。当时王安石博得神宗的信任和支持,极力推行变法,为破除障碍,在政府各部门不遗余力地清除异己。稳重的老臣纷纷离朝,御史台也遭到清肃排斥,继之身为谏官的是一群宵小之徒,整个官场闹得乌烟瘴气。面对纷扰的政治乱局和新法的诸多弊端,苏轼满怀忧思愤慨,给神宗皇帝上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万言书,广博的学问、冷静的推理、愤怒的争论、大无畏的勇气,在书中都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神宗皇帝当时根本听不进去。于是,苏轼再上第二书、第三书,慷慨激昂,发欲冲冠,直到熙宁四年(1071),他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出了一道“论独断”的乡试考题,这下彻底激怒了王安石,栽赃陷害打压排挤随之而来。心灰意冷的苏轼自知在朝已无立足之地,自请外任,赴杭州任通判,然后又知密州,政治生涯刚起步便遭遇挫折。
苏轼的才学当时已天下闻名,文坛领袖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书信中就大发感慨:“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才学如此,本该施展抱负建功立业,可是为了躲避朝廷争斗漩涡,苏轼从开封府推官到通判杭州,再知密州,十余年间,一直处于外放冷遇地位,虽然他尽己所能地兴水利、灭蝗灾、救弃婴、平盗匪,力保一方民安,但面对朝政的倾颓却无可奈何,有心无力。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构成了他所面对的第一重人生困境。这在词作中表现为“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疑问,“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忧虑。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一引《复雅歌词》,称神宗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称“苏轼终是爱君”。今天也有研究者认为,词中的“天上”“人间”正是朝廷与地方的象征,表达的是词人的忠君思想。这样的解读虽不无道理,但终究过于狭隘。王国维《人间词话》称:“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天上”“人间”的迂回往复,沉郁顿挫,正折射出了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造成的人生困境。
第二重人生困境便是“入世”与“出世”的困扰和挣扎。苏轼的思想相当驳杂,儒家思想构成了他思想的基调和底色,但释、道思想对他的影响同样深远。苏轼原本生性旷达,随性自由,“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即便是经过了官场的锤炼,仍久驯不化,“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游卢山次韵章传道》)“好僭议朝政,屡以此获罪”,却不知悔改,自言“受性于天,不能尽改”。(《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政治上的困顿失意,秉性上对自由放旷的追求,进一步加剧了“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兼济之志既难以实现,归隐之情便时常浮上心头。“病马已无千里志”(《和晁同年九日见寄》),“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寄黎眉州》),这些心迹表白,无疑是内心“出”与“入”矛盾的困扰,是欲进无途、欲退无由的挣扎,而这种种情思借由“乘风归去”“起舞人间”的意象寄托婉曲地表达出来。
第三重困境是亲人聚少离多的思念与煎熬。苏轼、苏辙两兄弟从小一起长大,一同参加科举,一路走来始终相扶相携,感情无比深厚。在《送李公择》中,苏轼感叹,“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在他看来,苏辙“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而在苏辙眼中,哥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宋史・苏辙传》评价兄弟二人称:“辙与兄轼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兄弟俩在准备制科考试时曾寓居怀远驿,当时便相约“功成身退,夜雨对床”,这成为他们在半世聚散沉浮中念念不忘的约定。苏轼任杭州通判期满,请调密州,“请郡东方,实欲弟昆之相近。”(《密州谢表》)因为苏辙当时任齐州掌书记。尽管密州和齐州相距不过几百里,但密州期间兄弟二人竟未能相见,“兼怀子由”所表达的正是对亲人深挚的思念之情。苏轼知密州时,双亲早已亡故,妻子王弗也已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人生的悲苦寂寥可以想见,特别是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对亲人的思念就更显深沉而热烈。“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样的质问,不正是对离别之情、思念之苦的感喟吗?词序中“欢饮达旦,大醉”,不过是一曲笔,当从反面来理解。“欢饮”多半是强作欢颜,难掩内心的悲苦和思念;“大醉”也不是率性雄豪,而是难以排解的愁苦对心灵的自我压榨,也许只有醉中才能得片刻解脱。
面对三重人生困境的挤压,苏轼既没有随波逐流屈己谄媚,以换取跻身朝堂的政治资本,也没有怨天尤人万念俱灰,堕入佛道的虚无缥缈,而是凭借深邃的哲思、旷达的胸襟,烛照宇宙、社会、人生的本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对宇宙人生常道的参悟,这世上没有绝对完满的存在,缺憾与不足乃是永恒的常态,入世苦,出世也苦,人生的一切“高处”之争,都是苦乐相伴、患难相随的。了悟了这一层,也就不必再纠结于天上人间的抉择,更不必沉溺于聚散离合的悲欢。苏轼正是凭借这样的哲思和非凡的艺术才华,在诗词的世界里最终完成人生的突围,化解人生的苦闷,重新回归内心的平衡。“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美好的祝愿洋溢着词人对人生常态常情的审美观照,是破解人生困境之后灵魂的安宁与愉悦,既充满了朴素的人间烟火气,又是那样超拔脱俗,绝无半点鄙俗之气。这是《水调歌头》的艺术妙境,更是苏轼非凡人格、伟大灵魂的真境。
因此,此词的审美意蕴不在于展示了理想与现实、入世与出世、团聚与分离的矛盾,而在于词人面对这些矛盾所造成的人生困境,如何实现自我突围,如何依靠深邃的哲思和超凡的人格对现实的矛盾作艺术的超越,并在这样的人生突围中达成对宇宙、社会、人生更高层次的认知,这才是作品的恒久魅力所在。东坡先生的中秋词,当作如是观。
(作者系辽宁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