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贝多芬诞辰二百五十周年 在“音乐考古”中还原大师和经典
【深度解读】
作者:王纪宴(北京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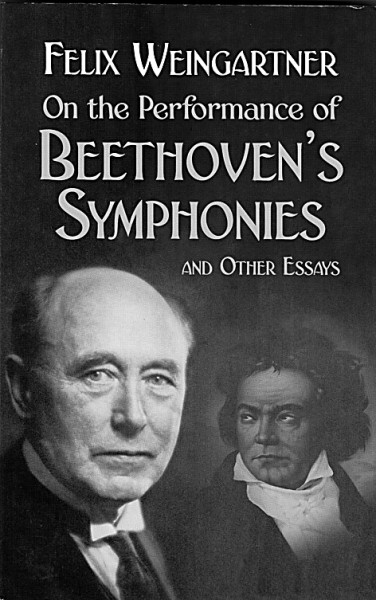
魏因加特纳《论贝多芬交响曲的演出》英文版封面 资料图片
今年12月16日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在重温经典之际,那些与贝多芬丰富音乐遗产相关的技术细节与轶事传闻,再次激发起人们求证还原的热情。
对20世纪人文科学诸多领域有着广泛影响的法国当代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他的《知识考古学》一书第五章“结束语”中提出了“考古学的对应空间”这一概念,虽然福柯并未对之进行详细论述,但在福柯称之为“考古学作为各种不同的话语实践特有规律的分析”语境下,“考古学的对应空间”在逻辑上也应该涵盖包括音乐学研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音乐演出实践在内的“音乐考古”。
作为探寻和发掘古代人类社会实物遗存的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概念的延展,“音乐考古”其实更接近“考古学”希腊语词源的内涵,即“研究古代之学”。在演出实践领域,“音乐考古”集中体现在肇始于19世纪并于20世纪发扬光大的“古乐运动”或称“本真运动”中。音乐学者和音乐家通过对博物馆里的古老乐器、作曲家手稿以及演出记录(包括费用账单)等浩瀚历史文献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让古老的乐器重新登上音乐舞台,而新制造复古乐器也加入古乐器行列,共同组成古乐团,以忠实于作品诞生年代的演奏手法和风格进行演奏,从而成为“本真演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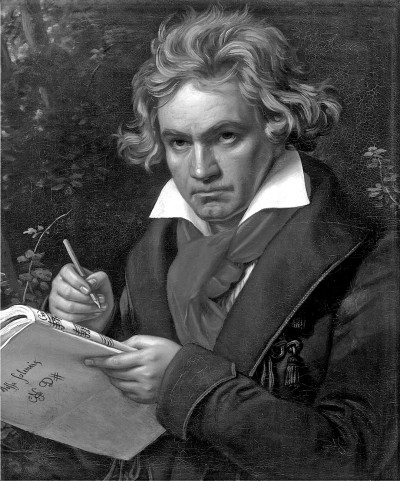
贝多芬画像 资料图片
1.古乐团的演奏与“命运”的初衷
古乐运动作为20世纪引人瞩目的音乐文化现象之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音乐学家威尔·克拉奇菲尔德在《复兴时代的风尚、信仰与演奏风格》一文中指出的:“在巴洛克音乐领域,已很少有现代乐器的录音。”其实古乐演奏远不限于巴洛克时期,在贝多芬音乐的阐释中,古乐运动也具有日益提升的地位。
在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的2020年,在古典音乐尤其是德奥古典音乐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唱片品牌“德意志唱片”(简称DG)发行的贝多芬作品全集中,九部交响曲的演绎出现了“双峰对峙”的格局:在柏林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现代乐团演奏录音之外,还有另一套录音,即约翰·埃利奥特·加德纳指挥他的“革命与浪漫管弦乐团”的古乐演奏。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纪念年的这一新气象,并非唱片公司的偶然之举,而是贝多芬音乐传播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的一个侧面,是“音乐考古”结出的丰硕成果。
毋庸置疑,对于为数众多的听者而言,古乐团的演奏会带来不同的管弦乐音色和速度(大部分古乐演奏都在速度上快于传统的现代乐团演奏,包括在慢乐章中),但古乐演奏的意义绝不限于这些方面。如同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关于“历史”所指出的:“应当使历史脱离它那种长期自鸣得意的形象,历史以此证明自己是一门人类学: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过去事情的新鲜感。”福柯在此处所用的“历史”这一概念,对应于音乐接受和阐释的历史以及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传统,其“长期自鸣得意的形象”同样遇到挑战和质疑,而背后的强大动力之一是“音乐考古”,它依赖于乐谱手稿等“物质的文献”而获得了一种让经典作品活力焕发的“新鲜感”。而获得这种新鲜感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恢复音乐中存在的福柯称之为“为了使事件的连续性显现出来而可能被回避、被抑制、被消除的东西。”
贝多芬作品中的一个典型例证来自他著名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这部交响曲曾被广泛地认为与“命运”的标题相连,事实上,时至今日,包括我国乐团在内的许多乐团在演出此曲时,节目单上仍会出现“命运”的标题,而在乐曲解说、相关书刊以及无数自媒体谈及此曲的文字中,“命运”的使用率相当高。但在学术研究领域以及主流唱片公司和乐团的文字中,“命运”的标题已经不再出现,这是“音乐考古”的贡献之一。而与有意识涤除对经典作品过度阐释的“去标题化”并行的,是在“音乐考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指挥家、演奏家对贝多芬笔下音符的更多尊重,对总谱的忠实。奥地利杰出的音乐学家弗朗茨·恩德勒指出:“直到古斯塔夫·马勒,人们在演出贝多芬的交响曲时首先想到的是改变贝多芬总谱上的原有配器。因为人们认定耳聋的贝多芬内心希望表达的要远远超越他那个时代所拥有的乐器和技法。”而这样做的一个理直气壮的前提,常常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贝多芬的英雄观念。对于第五交响曲,则是要体现“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的勇者气概。这种英雄观念成为福柯所称的“连续性”,为了体现音乐一气呵成的连续性,贝多芬在总谱上写下的音符需要改变。比如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再现部的副部主题,在总谱上为第303至306小节。在此之前的呈示部中,这一号角动机由圆号吹奏,但到了再现部时,贝多芬将它交给音色并不嘹亮的大管吹奏。于是,指挥家魏因加特纳在他的《论贝多芬交响曲的演出》中写下他深思熟虑的忠告:“副题之前的连接句在呈示部中原本由圆号吹奏,在这里改为由大管吹奏,这样做无非是为了避免配器上的困难。贝多芬不能放心地将这个连接句交给降E调圆号,因为他不希望用圆号的人工音来吹奏这个既无其他乐器陪伴又要激发巨大气势的乐句。他没有给圆号改调的时间,又不愿意为这几小节而多用一对圆号,所以,除了用大管之外,别无解决困难的出路。但是,与呈示部相比,再现部中用大管的结果是令人惋惜的,实际上简直有点喜剧成分。大管在这里的发音显得像是一位丑角出现于天神集会。两只圆号又在第306小节突然闯入,用它们的自然音吹奏sf(突强),这种突然的声音比前面响得出奇,因而加重了这种拙劣效果。”魏因加特纳坚信:“彻底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用圆号代替大管;假如贝多芬当时有我们现在的圆号,他一定也会这么做……唯有采用这个办法才能使这个主题获得它本来的音色和应有的尊严。”
从魏因加特纳时代(这位指挥家逝世于1942年)直到20世纪末,绝大多数指挥家,包括托斯卡尼尼、富特文格勒和卡拉扬,尽管他们被划分为“客观派”和“主观派”,却都按照魏因加特纳的上述建议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副部主题,而并不按照贝多芬总谱上写下的配器。“音乐考古”的践行者即所谓“古乐指挥家”和他们的古乐团颠覆了这一传统,他们的演奏依照贝多芬写在总谱上的音符,而不受“与命运搏斗”理念的“连续性”干扰。在英国的汉诺威乐团或比利时羽管键琴演奏家和指挥家约斯·范·伊莫希尔与他的“永恒之灵”等古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录音中,第一乐章副部主题开始由大管而非圆号演奏,而圆号在306小节的“突然闯入”,就是以那种十足的贝多芬式大胆手法呈现出来的。这一刻或许不那么具有响亮的“英雄”感,但却是严格依照贝多芬写下的每个音符和表情指示,表现出的是一种更具戏剧性的对比。这样的细节还原所引起的音乐表现上的变化,印证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在《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500年,从1500年至今》一书的观点:“最近人们燃起了对使用古老乐器演奏当时音乐的兴趣,结果发现乐器不仅仅是对音乐的发展,而且对音乐的含义都有很大影响。”

罗曼·罗兰 资料图片
2.罗曼·罗兰眼中的叛逆者和英雄
对贝多芬创作中细节的“音乐考古”,体现了福柯知识考古学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即“今后,文学分析……不是在将作者的生活和他的创作结合起来的交换手法中作者所塑造的人物作为单位,而是将一部作品、一本书、一篇文章的结构作为单位。”以作曲家的生平来解释其作品而或多或少忽视作为“文本”的乐谱本身,这样的做法同样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罗曼·罗兰视贝多芬为充满神圣色彩的叛逆者、受难者和英雄,他不仅在他的影响广泛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中,也在《贝多芬传》中对贝多芬进行文学化的塑造,而他对贝多芬音乐作品的阐释,同样富于文学化色彩。如第三《英雄》交响曲第一乐章,在再现部到来之前,有一个令贝多芬同时代人以及后世同行不解的地方:圆号吹奏的主部主题在小提琴演奏的和声尚未转到主调性时即开始,对于训练有素的听者,此处的感觉是圆号错误地提前四小节进入。在这首交响曲于1805年4月7日在维也纳河畔剧院首演时,贝多芬的朋友和学生(也是波恩同乡)费迪南德·里斯指出了这一点,引起贝多芬的不快,证明作曲家是有意为之而非错误。法国作曲家埃克托尔·柏辽兹以敢于打破陈规著称,但他对贝多芬在第三交响曲的这种做法同样不能理解:“要想给这一个音乐上的怪癖找到一个严正的辩解是有困难的”。罗曼·罗兰没有触及和声技术问题,而是赋予这一瞬间以富于画面感的阐释:“被打倒的战士想要爬起,但他再也没有力气;生命的韵律已经中断,似乎已濒临殒灭……突然,命运的呼喊微弱地透出那晃动的紫色雾幔,英雄在号角声中从死亡的深渊站起。整个乐队跃起欢呼,因为这是生命的复活……再现部开始了,胜利将由它来完成。”对于很多听者而言,罗曼·罗兰的描述与音乐极为契合,结果是,一旦读过这段文字,再听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想象力很难摆脱其影响。
音乐领域的浪漫观念有一个极具广泛性的体现,即通过作曲家的生平来解释和理解其作品。但这一点在贝多芬的D大调第二交响曲中遇到了问题。这部交响曲是从1801年开始写作的,作品大部分完成于1802年夏天和初秋,至10月最后完成。正是在这之前不久,贝多芬写下他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表达了他因听力出现问题而产生的绝望,同时也赞美了艺术的伟大和力量:“是艺术,只是艺术,才挽救了我的生命,因为在我没有创造出我感到是天意要我创造的一切之前,我是不能离开这个世界的。”第二交响曲被一些乐曲解释者称为“英雄的谎言”,就是因为贝多芬在他人生绝望的低谷中却创造出如此欢乐洋溢的音乐。英国音乐评论家巴希尔·迪恩曾指出:“18世纪的交响曲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的娱乐形式;而在浪漫主义者那里,它是以宏伟的气度进行自我表达的媒介。对于贝多芬而言,两者都不是。它是公众的作品,并非私人性的。它并不表现他当时的个人境况,他也不用它去象征某一桩亲密的人际交往。第二交响曲写于‘海利根施塔特遗嘱’时期;此外并未有哪位女性曾得到过他题献一部交响曲或一首序曲的恭维之词。贝多芬的公众是人类,他是人类的代言人。在他的交响曲和序曲中,他宣告了自己对于生命的观念,这种观念,他相信,具有广泛普适性:对大自然的爱,对和平、自由与兄弟情义的渴求,冲突、挫折与胜利的现实。为了实现他的目标,他必须锻造一种新的交响音乐语言,这种语言的冲击力更为直接,而同时又承载着到那时为止尚未被探索的表现幅度。关于他的交响曲的故事就是关于他创造和拓展这种语言的故事。”
英雄的观念和形象,与贝多芬如影相随。音乐学家亚历珊德拉·科米尼在她的近500页专著《变化的贝多芬形象——神话制造研究》中指出,贝多芬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贝多芬神话”的参与制造者,这样的神话有助于他的音乐事业。在20世纪上半叶,像加拿大钢琴家格伦·古尔德这样有着敏感的当代心灵的音乐家,并未受“音乐考古”理念影响,但以他身为音乐家的直觉,他感到贝多芬的雄浑激越中有一种令他难以接受的咄咄逼人。而瓦格纳的观点显示出这位音乐巨匠的非凡洞悉。当音乐家和学者们为贝多芬第三《英雄》交响曲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究竟为哪位英雄送葬而观点不一时,瓦格纳在1825年的《论贝多芬作品中诗的内容》一文中触及一种更朴素同时也更深邃的观念:“英雄一词,蕴含着最广泛的意义,绝不是仅仅指作战的英雄。如果我们广泛地理解英雄的意义是完人,他显示着最充实、最强壮的,一切纯粹属于人类的感情——热忱、苦痛和毅力,那么,我们就可以正确地把握住作品内容的要领。”

波恩贝多芬音乐厅前的贝多芬塑像 王纪宴摄
3.关于贝多芬失聪与否的考证
“音乐考古”也在重塑贝多芬的形象。今年初,一篇标题为《重大发现——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首演时“并非完全失聪”》的文章,介绍肯特州立大学音乐学教授西奥多·阿尔布雷特的观点,“贝多芬在他的职业生涯晚期可能并没有完全失聪”。这位学者在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贝多芬同时代人的记述后,认为有新的证据显示,“贝多芬不仅在1824年5月的第九交响曲首演中没有完全失聪,而且至少两年后他还能听到(尽管越来越微弱)。”直到贝多芬于1827年去世前不久,他的左耳仍能听到一些声音。阿尔布雷特由此断言:“这将会让每个人匆忙修改关于贝多芬的传记部分。”
长期以来,对于贝多芬,包括很多专业音乐家在内的人都习惯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贝多芬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双耳失聪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是何等令人赞叹、不可思议的奇迹!一个完全听不到声音的人却能写出一部又一部恢宏壮丽的不朽杰作!而更加“专业”的观点虽然并不认为一位训练有素且积累了足够经验的作曲家在失去听力的情况下创作交响乐是无法解释的,但有另一种更加诗意化的提升,即贝多芬由于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不得不与身边的音乐生活失去联系,这反而让他免受音乐时尚的影响,无视当时风靡维也纳的“肤浅音乐”(以罗西尼歌剧为代表的意大利音乐),进而能自由地“听从内心的召唤”,创作出超凡脱俗的音乐。
实际上,严格地说,阿尔布雷特教授的观点并非“重大发现”。前文提及的恩德勒在所著《维也纳音乐史话》一书中写道:“贝多芬从未完全失去听觉。他直到逝世前仍可听到断断续续的音乐,还能听明白人们大声说话。但这对由于病情严重且无法医治而倍感孤独的他来说是无济于事的。”这说明,在贝多芬生活、创作和长眠的这座音乐之都,将贝多芬视为一位在耳聋状态下创作出众多不朽杰作的音乐家,是相当广泛的共识。这也反映了从传记到文艺作品和大众话语一脉相承的对历史真实的背离。在同时代人对贝多芬耳疾与听力状况的记录和描述中,贝多芬的学生卡尔·车尔尼被认为是最客观的。伊莫希尔在他的《我们真的了解贝多芬的乐团和他的音乐吗?》一文中有一章标题为“九部交响曲与贝多芬的耳聋:神话与现实”,其“音乐考古”的依据即来自车尔尼的记述。车尔尼告诉人们,创作前八部交响曲的贝多芬虽受耳病折磨,但还有听力。在创作第九交响曲的前三个乐章时,也还能依稀听到,但在时隔数年后创作这部交响曲的最后一个乐章即出现著名的《欢乐颂》的乐章时,贝多芬才基本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了,这也是导致这个乐章在演出呈现中技术困难大大超过其他乐章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虽然此时的贝多芬就艺术造诣而言已经是炉火纯青的大师,但听力的丧失还是让他在配器上出现“失算”。
为什么在近两个世纪中,贝多芬的“亲传弟子”车尔尼的记述并不能与“耳聋大师”的神话抗衡?原因之一或许在于浪漫的英雄传记观。同为作曲家,失去听力的不幸者并非只有贝多芬,交响诗《我的祖国》的作曲家斯美塔那在晚年完全失聪,他曾悲哀地写下自己的感受:“脑袋里的呼啸轰鸣使我感到自己好像站在一个巨大的瀑布下面……作曲时耳鸣得非常厉害。”虽然《沃尔塔瓦河》是音乐会上演出频率最高的名曲之一,但世人对于其创作者耳聋的关注度远不及对贝多芬的关注。贝多芬在一代又一代的人心目中成为遭遇不幸而顽强与命运搏斗、“扼住命运咽喉”的强者和英雄的化身。而在这一趋势中,他的耳疾和耳聋的程度,被不同程度地渲染和夸张。
“音乐考古”背景下的贝多芬纪念让我们认识到,更趋客观真实的贝多芬形象并不影响这位作曲家的伟大,贝多芬的伟大并不仰赖于“贝多芬神话”,而是来源于贝多芬留下的音乐杰作。正如伊莫希尔所认为的,“没有什么比严肃对待其音乐能更好地体现对一位作曲家的尊重了”。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7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