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远去,奔腾起英雄的史诗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英雄气”似乎正变成一种越来越稀有的东西。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够“英雄”。恰恰相反,今日的中国处在国力上升、实力增强、秩序稳定、稳步繁荣的阶段,换言之,今天的读者们是生活在“盛世”之中。问题是,“盛世”本身便是英雄形象的一种,一切伟大的历史实践自身便是英雄感的重要来源,这关乎历史判断和时代感知;但落实到文学艺术,要将这种总体性的“英雄气”具体凝固为形象、动作、行为,其实是不容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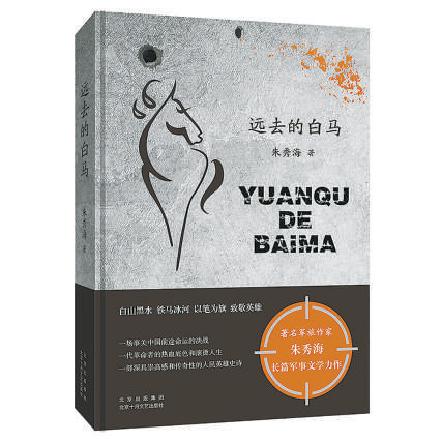
《远去的白马》朱秀海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反倒是在动荡的时期、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在所谓的“乱世”,“英雄气”更容易具化为人与事。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世界的秩序重新洗牌,一个人或将能以极富冲击力的方式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并以此成为秩序重塑过程中重要的影响因子。这正是我们直到今天都对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情有独钟的原因——此类故事以最具象、最惊人且感人的方式,诠释了英雄主义,并且这英雄主义接通着历史叙事的主脉,在现实逻辑上与今日之中国一脉相承。
传奇浪漫与质朴真实的辩证统一
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显然满足了我们对“英雄气”的想象与期待。它的故事是跌宕的:一支几乎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在极度险恶的战争形势下,不仅生存下来,还一路打成了能干硬仗的精锐部队。它的人物是传奇的:一位女性、一位本不属于作战部队的“临时工”“编外人”,成为了这支部队里的重要角色,一次次挽救队伍于危急存亡之际。这个故事的坐标牢牢扎在历史主脉上:主人公赵秀英跟随队伍完整地经历了转战东北、建立根据地直至打赢“辽沈战役”的全过程,包括以“零距离”方式直接参与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但在“建立新中国”这样恢宏浩大的叙事主脉之外,同样闪耀着光芒的,还有人物细腻柔软的内心情感世界:赵秀英与一个个身骑白马的英雄男子间的故事牵绊、她内心世界的义无反顾和百转千回,在荡气回肠的同时亦令人垂泪感怀。
有评论家在谈论这本书时用到一个词叫“侠骨柔情”。我对此非常认同。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传奇性与浪漫感二者,像DNA双螺旋一样拧在一起,相互对冲又相互融合。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对《远去的白马》最直接、最强烈的感受,都会与“传奇”“浪漫”两个概念有关。然而在我看来,于此二者的背后,从底色上真正将整个故事支撑起来的,却是不易察觉,但又扎实深刻的“真实性”。传奇浪漫与质朴真实二者,以一种二律悖反般的方式,构成了辩证统一。
真实到什么程度?真实到这个充满英雄气的故事,在很多地方看起来似乎一点都不“英雄”。从胶东转战东北时,情况紧急,登船的队伍被挤得七零八落,登船人员甚至需要从栈桥上像下饺子一般往船上跳。到了东北,情况没有从容多少,许多队伍也是临时重组,开上战场。这种“乱哄哄”“拉郎配”的另类战争画风,多少有些荒诞甚至带点“喜感”,却是建基于真实的历史情况,以一种看似轻松热闹的方式,折射出当时战事的紧急乃至悲壮感。
对战争的正面描写也是一样。三十七团初入东北,迎头就在摩天岭之战遭遇了敌人的精锐部队。这一仗打起来,情形居然是这样的:“山头战壕里的老少游击队员们既没有见过这么猛的炮火轰击,更没见过这么多自动化武器一起打响的威力,胆小的,渡海前刚入伍,炮声一响什么都忘了,丢下阵地撒丫子便跑,没跑的见了,也吓得跟着跑。”这样的情形大大超出了我们以往的理解惯性,但背后有着充分的真实逻辑:“打游击战时他们一直这样,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今天逃走是为了明天接着跟日本人干……拔腿就跑都成了习惯”。现在,战争的情况和需求不一样了,有很多事情,这支队伍要从头学起:从只会打游击战开始,慢慢学会打防御战,然后再学会打攻坚战、成为真正的主力部队……一步步从零发展到无限。
这一“英雄部队”的成长全过程,在《远去的白马》一书里呈现得特别扎实,既速写了宏大的战争场面,也雕琢了微观的行动细节,不论在文本的内部逻辑还是读者的心理感受层面,都展现出巨大的真实感。恰恰是这种真实,为书中所有的不可思议和英雄传奇,赋予了雄辩的说服力。因此,尽管第一眼看去,这是一部“飞在天上”的作品,但它同时(甚至“首先”)是一部“走在地上”的作品。
从“小的偶然”到“大的必然”
如果说,“传奇”与“真实”的辩证统一,奠定了《远去的白马》内在的气质,那么另一组同样辩证统一的概念“对子”,则构成了小说叙事具体的推进动力。这一组“对子”,我称之为“偶然”与“必然”。
从情节上看,《远去的白马》是从一系列“偶然”、一系列误打误撞展开的。整个故事的逻辑起点非常细小甚至带有一点儿荒诞感,就是“嫁错郎”和“上错船”。赵秀英与抗日英雄结为夫妻,因战火离散后才发现对方是走错了洞房。她本也不需要开赴东北,却在码头上阴差阳错地被赶上船,就此变成了解放战争中的“支前大姐”。这类情节的发生,本身具有极强的偶然性,背后却包含着巨大的必然性;看起来是“将错就错”,细想却是“由错入对”。赵秀英真的嫁错人了吗?骑白马的英雄走错了洞房,但书中其他几位英雄也都与白马有关,赵秀英的确把心许给了他们——并非世俗意义上的夫妻之情,但是却更博大、更真实、更崇高。赵秀英真的上错船了吗?事实上,即便不去辽沈战役前线而留在山东,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象,她必定会出现在淮海战役的支前队伍之中。在这个故事里,很多事都错了,但都“错”得“对”了;很多事“想不到会是这样”,但又似乎“原本便该是这样”。《远去的白马》乃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它从小的偶然去写大的必然,通过小的阴差阳错写出了大的天地玄黄。
这是事件“小逻辑”和情节“大逻辑”之间,巧妙的错位及重新的榫合。整部小说的情节,由此不断地向下推进,情感势能越推越高。书中有一处细节格外能够体现这种错位及榫合的力量。书中的人物,上到军队首长、下到基层指战员,都反复地提到过一种观点,那就是革命终将胜利,但道路难免曲折,我们这一代人不要指望自己真能活着看到革命胜利。
这并不是随便说说。小说里,千秋在塔山阻击战之后,捡到了一台收音机,通过广播,得知了锦州大捷的消息。直到这一刻,直到东北战场大局已定,他才第一次真的相信,“我们共产党这回真的要成事儿了”。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甚至是不合理的:自古打仗都是为了赢,是为了活下来成为胜利者,怎么可以有这么一个人、这么一群人,他们把自己的命都给出去了,却一直都没敢指望“成事儿”?或者反过来说,他们并不奢望自己享受到胜利,却怎么竟依然能奋勇向前?一个人需要有多么大的信仰,才能不指望赢而仍然去打仗!我们几乎从没见到过这样的一种人,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如此的没有信心,却又是如此的有信心。这是何其惊人的力量:一种史诗般的“信”,它是如此的坚定和无保留,以至于要通过“不信”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
白马象征巨大的“战争潜力”
最后,说说“白马”这一核心意象。白马是中国古典文化里极富魅力的符号,它意味着出挑与俊秀,登场亮相便与英雄的形象相关。然而,这只是表层的、自动化联想式的意义;它的背后,还有着更技术化、也更深远的想象和阐释空间,那便是一种伟大的平凡。古代文化为什么强调白马这个形象?因为骑白马的,往往是猛将或者精锐部队,白马形象带有震慑力。那么白马为什么“白”?其实是因为其基因内出现了极特殊的异变,马的毛发滤泡中黑色素细胞在动物早年就“罢工”、无法产生黑色素。这种基因异变的概率很低,很多匹正常的马中,才会出现一匹白马。因此,当你看到一匹白马、一队白马,瞬间就会意识到,它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多的、数不清的马。因此,白马真正的震慑力,来自它背后巨大的“马的潜力”,换成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来自于白马所象征的巨大“战争潜力”。
在《远去的白马》里,在真实的历史上,这个“战争潜力”,就是人民。因此在这本小说中,别看骑着白马的人都是出挑的英雄,但白马意象里真正包含的震慑人心的力量,其实也来自赵秀英这样无数甚至可能无名的支持革命的人民。不久前,我在徐州参观了淮海战役纪念馆,那里有一整面墙,都是革命胜利后补拍的淮海战役支前民工们的个人照片。他们大都是从山东出发去支前的,来自小说中赵秀英大姐的故乡。照片上,他们每个人都穿着草鞋。而在我的心里,他们每个人都骑着白马。(李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