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乐理念”到“维也纳之声”
维也纳爱乐乐团创建180周年
从“爱乐理念”到“维也纳之声”
作者:王纪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
“这个乐团的演奏体现着维也纳这座全世界公认的音乐之都的灵魂。乐团自身已经成为一个伟大传统的当之无愧的守护者。”老一辈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对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这一称赞,不仅能够代表众多音乐家的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无数听众的共同心声。2022年3月28日为维也纳爱乐乐团成立180周年纪念日,回顾这个艺术团体在180年间走过的历程,也是世界各地“维也纳之声”热爱者的共同愿望。

奥托·尼科莱,油画,罗伯特·施特赖特根据约瑟夫·克利胡贝尔的石版画像作 资料图片
Ⅰ、180年的足迹
“1842年3月28日,维也纳音乐史上一个神奇的日子——而且远不止于此。”翻开克里斯托夫·瓦格纳-特伦克维茨所撰写的《一种声音传统:维也纳爱乐乐团简史》一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一行文字。这一天是复活节,中午12点30分,在皇宫大舞厅,“宫廷歌剧院乐团全体成员”在剧院首席指挥奥托·尼科莱的指挥下演出了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音乐会。音乐会节目单上的曲目包括贝多芬的A大调第七交响曲和《莱奥诺拉》第三序曲,但实际上在音乐会演奏的并非《莱奥诺拉》第三序曲,而是《莱奥诺拉》第一序曲。曲目的选择体现了音乐家们的共同追求——“旨在弘扬贝多芬的交响音乐遗产”(作家汉斯·魏格尔语)。
这一年距贝多芬辞世几乎恰好是15年,而距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1824年5月7日的首演将近18年。在那场被贝多芬的学生卡尔·车尔尼描述为“万众期待已久”的音乐会举行时,维也纳虽然有着日趋丰富的音乐生活,交响音乐会频繁举行,但那里既没有一座专业的音乐厅,也没有一个常设的交响乐团。当举行重要音乐会,特别是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样需要庞大阵容的作品时,需要以歌剧院乐团为主体,增加更多演奏者,包括业余人士。所以,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首演之夜的维也纳科恩特纳门剧院,既有维也纳当时最出色的专业演奏家,也有临时招募的业余演奏者,而这种做法在当时是音乐界的惯例。钢琴家鲁道夫·布赫宾德在《我的贝多芬:与大师相伴的生活》中写道:“我们所知的现代音乐会行业中的管弦乐团,在那个时代(贝多芬的时代)并不存在。今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或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均由歌剧院阵容中脱颖而出,成为定期演出的职业乐团。”
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的历史可上溯至1548年,相比之下,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成立时间晚了将近三个世纪。但后者的根源也可以追溯得更久远。奥地利音乐评论家弗朗茨·恩德勒在《维也纳音乐史话》中指出:“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把维也纳歌剧院的创始时间追溯到巴洛克时代。可以说,当时的各种歌剧演出团体就是维也纳歌剧院的前身,那时在皇帝的热情支持参与下,维也纳的歌剧演出已成规模。”虽然如此规模的上溯不免有些幻想色彩,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演出对于“爱乐理念”的激发,以及对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诞生具有重要意义已成为共识。1833年,德国作曲家和指挥家弗朗茨·拉赫纳进行了组建乐团的尝试,他召集宫廷歌剧院乐团的演奏家相继举行了4场音乐会,每场音乐会都演奏贝多芬的一首交响曲,这种做法已经高度接近9年后的维也纳爱乐乐团。但之所以1842年3月28日才被认定为维也纳爱乐乐团正式成立的日期(虽然当时乐团还没有冠以“维也纳爱乐乐团”之名,音乐会也没有像后来那样命名为“爱乐音乐会”),是因为正是这场音乐会确立了一直秉承至今的“爱乐理念”,那便是只有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之前为宫廷歌剧院)乐团的签约成员才能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一员;乐团的艺术、行政和财政完全自主;乐团的所有决策由全体成员投票产生(包括歌剧院演出之外所有演出的曲目和指挥人选);乐团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由投票选举产生的12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承担。
这种“爱乐理念”主导着维也纳爱乐乐团艺术活动的所有方面,按照恩德勒的说法,这种理念“为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了其他大型乐团所不具有的优势与特权”,最主要的是,作为真正的私营机构,在法律规定之内,乐团的行为和活动不为外界所干涉。但“理念”与实践并非没有差距,在乐团的180年历史中,不可避免地有过低谷。在1842年至1847年的5年间举行了11场“爱乐音乐会”,那之后,乐团一度陷入沉寂状态,甚至濒临解散。从1854年至1857年,维也纳宫廷歌剧院常任指挥卡尔·埃凯尔特指挥了少量音乐会。1860年,埃凯尔特升任宫廷歌剧院院长后,相继指挥了4套“联票音乐会”,自此时起,乐团的演出持续进行,再未中断。正因为这样,尼科莱被视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创建者,而埃凯尔特则作为使乐团“重生”的人物同样赢得乐团的敬重。
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黄金时代”始于1870年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大厦的落成,正是作为这座宏伟建筑最主要部分的“金色大厅”,使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声音潜力得到充分发挥,无论对于乐团还是听众,在声音体验方面变化之巨,令曾任乐团主席的赫尔斯贝格发出“这个乐团在音乐之友协会大厅之前可曾存在”的感叹。
虽然“爱乐理念”久已深入人心,爱乐音乐会已成为维也纳以至世界各地艺术水准和知名度最高的演出,但直到1891年,在莫扎特逝世100周年的音乐会上,乐团才开始正式使用如今我们所熟悉和习惯的团名——维也纳爱乐乐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爱乐乐团与许多艺术机构一样,度过了一段艰辛岁月。国家歌剧院的犹太艺术家遭到纳粹分子解雇,指挥家富特文格勒为保护乐团演奏家,曾提出过一份名单,保护有犹太血统和与犹太人有婚姻关系的音乐家,后世称之为“富特文格勒名单”,它虽然远不及“辛德勒名单”闻名,但其中透出的关怀和温暖同样令人敬佩。作为建团180周年的纪念活动,维也纳爱乐乐团以独特的方式缅怀历史——以17块纪念石怀念在纳粹时期受害的乐团成员及其家人,今年2月17日乐团在金色大厅排练时,这17块纪念石就摆放在舞台前,今后它们将永久铺设于死难者在维也纳的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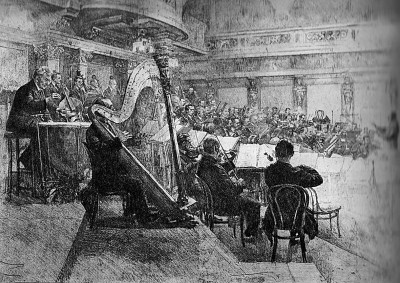
表现维也纳爱乐乐团在金色大厅演出的著名蚀刻画,费迪南德·施穆策作于1923年 资料图片
Ⅱ、“没有领导者的团体”
恩德勒在《维也纳音乐史话》中认为,维也纳爱乐乐团作为自治团体其实不可能真正我行我素,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乐团的成员均来自国家歌剧院,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歌剧院院长和音乐总监或首席指挥。
在维也纳爱乐乐团前60年历史上,除了临时替代因病不能登台的尼科莱担任指挥的格奥尔格·赫尔梅斯伯格和作为客座指挥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之子齐格弗里德·瓦格纳,乐团音乐会的指挥均为宫廷歌剧院指挥和音乐总监,而乐团自身不设音乐总监或首席、常任指挥之职,这与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交响乐团的做法不同。从1903年开始,乐团逐渐开始邀请更多客座指挥,但直到1933年之前,仍由一位固定指挥(通常为歌剧院音乐总监、院长或首席指挥)负责指挥乐团全年的联票系列音乐会。
从1933年起,固定指挥不再设立,每场音乐会都由乐团邀请客座指挥。这也就意味着,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的所有指挥家都是乐团邀请的客人,而非艺术或行政上的领导者。曾负责维也纳爱乐乐团媒体联络的打击乐声部成员沃尔夫冈·舒斯特在2000年的一次采访中说:“卡拉扬有一次曾这样说到柏林爱乐乐团:我创造了我的乐器。我们(维也纳爱乐乐团)可不想做任何人的乐器,我们想表达我们自己的个性,同时享受12或14位世界上优秀指挥家的变化风格。”
这样的体制无疑使维也纳爱乐乐团有了比任何其他乐团都更多的独立精神和尊严,用乐团成员的说法就是:在这里,指挥台上的人发号施令是不可能的。但这有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合作上的问题。
赢得维也纳爱乐乐团衷心爱戴的指挥家不可胜数,包括被视为乐团创始人的尼科莱,尽管当初他是对“爱乐理念”最不热心的人之一,他与乐团合作的时间也不长,但这位并非维也纳本地人的作曲家和指挥家始终在维也纳爱乐乐团享有特殊地位,乐团的系列音乐会中以尼科莱命名的音乐会总是深得乐团重视。尼科莱根据莎士比亚《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创作的同名歌剧序曲,是乐团最喜欢演奏的乐曲,几乎在乐团和尼科莱的任何重要年份都要出现在音乐会曲目中。1992年维也纳爱乐乐团成立150周年,卡洛斯·克莱伯指挥的新年音乐会以《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序曲作为整场音乐会的开场曲;2010年,尼科莱诞辰200周年,乔治·普莱特指挥的新年音乐会下半场以这首序曲开场;2017年,维也纳爱乐乐团成立175周年,古斯塔夫·杜达梅尔指挥的新年音乐会曲目中虽然没有出现《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序曲,却有这部歌剧第三幕中的优美合唱《月亮升起》。
汉斯·里希特担任指挥的两个时期被乐团珍视和缅怀,公认是艺术上的黄金时代,而马勒担任指挥的短暂时期却颇有争议。虽然马勒在乐团中不乏支持者,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他妹夫的乐团首席阿诺德·罗泽,而且,在1900年6月马勒与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之旅中,乐团陷入财务困境,是马勒为乐团筹划到解困的经费。在对经典作品尤其是贝多芬音乐的诠释方面,马勒与乐团所取得的成就也得到公认。如1899年11月5日马勒与乐团合作演奏的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赢得评论界盛赞,罗伯特·希尔什菲尔特在《维也纳晚报》上发表评论,写道:“命运不再‘敲门’,它将门撞倒在地。”但由于马勒在艺术上的严格要求和他与乐团音乐家相处的方式,使得他与乐团的关系日趋紧张,导致马勒在短短两年多之后便不再担任爱乐音乐会指挥。对于乐团一向引以为荣的传统,马勒的一句话为乐团带来的伤害持续很多年挥之不去——“你们所说的传统,经常不过是敷衍了事”。
半个多世纪后,还未成为大师级指挥的匈牙利人乔治·索尔蒂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为迪卡唱片录制瓦格纳的巨作《尼伯龙根的指环》时,切身感到了马勒这句话的所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录制“四联剧”的第二部《女武神》第三幕“女武神之骑”时,“铜管组漫不经心地演奏主要动机,将附点八分音符奏得太短,将十六分音符奏得太长。而铜管演奏家们的态度是:吹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当索尔蒂坚持要他们演奏得准确时,遭到演奏家们的抵触。指挥台上的索尔蒂分明感到乐团这样一种态度,那就是“我们懂的比你多”。而一旦遇到指挥与乐团在对音乐的理解和处理上不一致的情况时,乐团的演奏家们马上认定错在指挥。在1972年录制莫扎特的歌剧《魔笛》时,第一小提琴声部一位成员居然在演奏中突然起身,说了句“这活儿我不干了”便拂袖而去。而索尔蒂所能做的只能是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指挥。索尔蒂继续写道:“我一向听说的都是关于有些指挥怎么任性自负滥发淫威的,殊不知有些乐团成员也会让指挥深受伤害。”在索尔蒂心目中,有些年里他最喜欢的维也纳的街道是前往机场的路——终于可以离开了!
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有过很多合作的意大利指挥家卡洛·马利亚·朱利尼发现,在他指挥这个世界顶级乐团时,乐团的演奏家们有一种开启“自动运行模式”的倾向。而这种模式,即使像富特文格勒这样备受敬重的指挥大师也会遇到。瓦格纳-特伦克维茨在《一种声音传统:维也纳爱乐乐团简史》中告诉读者这样一件并非趣闻的事:某晚,维也纳爱乐乐团在富特文格勒指挥下演奏约翰·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乐团演奏家们决定给这首熟悉的圆舞曲多加点“摇曳感”,而不是完全跟着指挥的拍子。当乐团中有人在音乐会后问富特文格勒对演出的感受时,大师回答:“很棒!我就是照你们演的指挥的。”
在历数包括卡尔·伯姆、卡拉扬、伯恩斯坦、克莱伯、马泽尔、穆蒂等一众世界顶级指挥家与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合作后,瓦格纳-特伦克维茨在《一种声音传统:维也纳爱乐乐团简史》一书中竟写下了“爱乐乐团需要指挥吗?”一节!而我们读到,早在富特文格勒“照你们演的指挥”之前,瓦格纳1876年在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乐池中指挥他的《罗恩格林》时,就以他的“不作为”印证了指挥的“多余”。在奥特鲁德与艾尔莎二重唱的尾奏中,瓦格纳将手中的指挥棒放在谱台上,不再指挥,面带微笑地看着眼前的乐团“自动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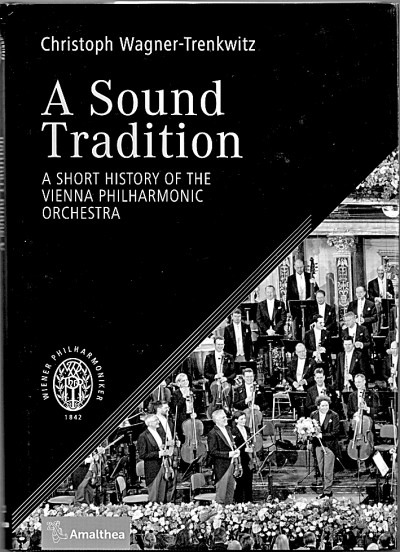
瓦格纳-特伦克维茨著《一种声音传统:维也纳爱乐乐团简史》 资料图片
Ⅲ、音效的秘密
维也纳爱乐乐团最鲜明的艺术风格是闻名于世的“维也纳之声”,即“Wiener Klang”,这种声音对于熟悉管弦乐团声音的古典音乐爱好者而言有着极高的辨识度,也为无数指挥家所称赞。
祖宾·梅塔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钟情于维也纳音乐那种丰满柔和的声音”,他指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声音。研究“维也纳之声”的构成原因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学术课题,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的格雷戈尔·维德霍姆所著的《维也纳音色风格》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弦乐、木管、铜管尤其是特征明显的“维也纳圆号”以及定音鼓,均作为“维也纳之声”的构成因素被深入研究。此外还包括维也纳爱乐乐团不同于世界各国乐团的标准音音高,即由双簧管吹出的为整个乐团定音的A4为443赫兹,而其他乐团通常为440赫兹。还有乐团在舞台上的声部布局,尤其是人们熟悉的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上,低音提琴声部在乐团后方排为一列正对指挥和听众的做法。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维也纳之声”与金色大厅共鸣丰富的音效密切相关。
但这一切似乎都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维也纳之声”的秘密。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排列,即使在金色大厅也并非一成不变,低音提琴有时也会像很多乐团那样位于舞台右侧。而当维也纳爱乐乐团在金色大厅之外演出时,“维也纳之声”依然不失其鲜明。对于笔者,最早有这种感受是在1998年5月28日晚,在泰晤士河南岸的皇家节日大厅,小泽征尔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和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坐在2层65排G33号的笔者强烈感受到,即使在这座被伦敦人批评为音效发干的大厅里,“维也纳之声”依然有着巨大的魅力!两天后评论家布莱恩·亨特在《每日电讯报》上的评论让笔者感到前所未有的共鸣:“没有哪位指挥家能让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奏听起来不像它自己而像任何其他乐团……各种乐器的音色丝毫不失去自身的辉煌,同时又响亮地融为一体。”
“维也纳之声”不仅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最擅长的德奥作曲大师(尤其是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布鲁克纳、马勒、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中有着魅力独具的体现,在演奏世界各国各时期的音乐时也总能带来与众不同的体验,如哈恰图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他脍炙人口的《马刀舞曲》,那种粗犷之风通过“维也纳之声”而传递,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文化融合感。而像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这样被视为通俗小曲的作品,老一辈指挥大师汉斯·克纳佩兹布什在1960年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以异乎寻常的宽广从容速度录下的演奏,有一种在任何其他演奏中都没有的雍容高贵气度和激动人心的美感。
当然,“维也纳之声”最广为人知的体现是“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父兄以及兰纳、赫尔梅斯伯格、齐雷尔、莱哈尔等作曲家的舞曲音乐或者说轻松音乐,一年一度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在全世界90多个国家直播或转播,不仅足以证明“维也纳之声”的魅力,也让人们相信:古典音乐并非很多人心目中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动听的“维也纳之声”会让音乐变得更美妙,更亲切。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31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