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二花:我的小说想表达人的力量
认识苏二花,是在山西省作协开会的时候。
第一次见面,她很热情,穿得也很简单,但是很有风格,一看就是黄土高原上的女人。她的中篇小说《社火》获得赵树理文学奖以后,她说当时心情很激动,因为那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同时也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攀登新的高峰做好了准备。
2017年正月的一天,苏二花和一帮朋友去太原娄烦龙泉村转九曲看社火,晚上有个老农画地狱图时,她萌发了写这部小说的念头。为了使创作更加接地气,她去龙泉村深入采访,获得第一手资料,作品非常扎实。赵树理文学奖获奖评语这样说,“《社火》以新颖的视角描写奔赴故乡途中的‘我’与大哥不同处境的心路历程、生与死的纠结。最后以正月初九的一场社火展现了众生对生、对死的庄严膜拜和苍凉心境,使作品的叙述超越了具体的人事,升华为具有仪式感的人生体悟,表现出生命贯通时空的不朽意义。”

苏二花,山西代县人。山西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小说发表在《都市》《山西文学》《黄河》等杂志,有作品被《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出版小说集《社火》。2016-2018年度,获得“赵树理文学奖”。她说,这次获奖只是个起点,会让她以后在文学道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自信。
作品中的龙泉村在娄烦 但此龙泉村已非彼龙泉村
山西晚报:您的中篇小说《社火》获了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说说当时的感受。
苏二花:
当时觉得挺意外的,说实话根本没想到。《社火》是2017年发表在《山西文学》上的中篇小说,没想到2019年获了奖。对我来说,获奖是一种鼓励,有了这种鼓励,在以后的文学道路上会走得更自信、更坚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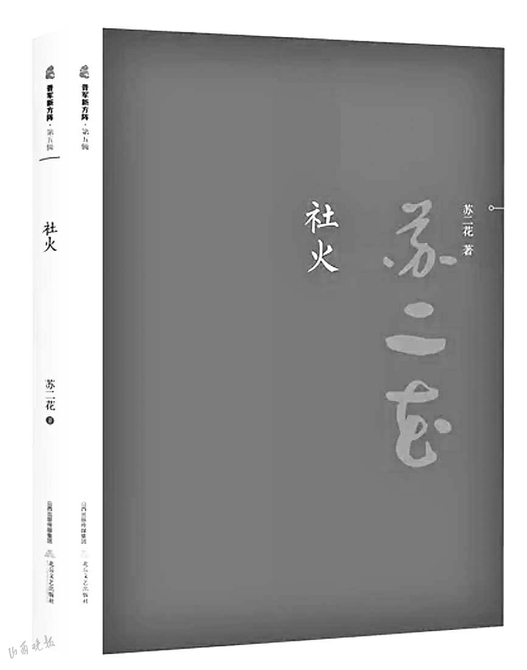
山西晚报:这部小说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苏二花:
这部小说有两万字,主要写的是龙泉村传统节日“禳瘟会”。“我”肚里有个不想生出来的孩子,“大哥”是个胃切除的癌症晚期不想死的患者,我们在城市受尽了伤,腊月的时候终于回到龙泉村,找到我们的老父亲。到正月初九这天,在传统节日“禳瘟会”上,父亲带我转了“九曲黄河阵”,消除了“我”的心结。之后,父亲又画下地狱图。在父亲的引导下,生的想生,死的也能安详面对死亡。
山西晚报:一说“社火”,总和过年分不开。这里的“社火”有哪些不一样?
苏二花:
传统节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能形成整个民族的集体认识,正是因为它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小说里的“禳瘟会”是“社火”中的一种,小说人物在这个传统节日里得到救赎。
山西晚报:作品中的“龙泉村”是个什么地方?
苏二花:
小说是虚构文学,地名和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在现实中确实有这么一个存在。2017年春节期间,我和几个朋友去太原娄烦县静游镇龙泉村看社火,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地狱图。但写在小说里,此龙泉村已非彼龙泉村,它更应该是个虚构的场景,是单独存在于小说里的龙泉村。
要能让我写作顺利且快乐,我就写 灵感来自于看老农画地狱图
山西晚报:为什么想起来创作这样一部小说?
苏二花:
和其他任何文学作品一样,小说也需要灵感。这个小说不是我想要去创作,而是遇到了合适的题材和合适的时间。说到底,灵感也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只要在写小说的路上,那这条路一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我觉得小说首先是语言的艺术,我的小说不是主题先行,而是文本先行。只要能让我写作顺利并且快乐,我就写;如果不是,那我就不写。而“社火”的创作,就是在这样一种愉快的状态中进行的。
山西晚报:那就说说您这个灵感吧。
苏二花:
2017年正月初八的下午,朋友们提议一起去龙泉村转九曲看社火。说走就走,我们立刻开车出发,赶往龙泉。到了那里已经五六点了,黄昏时分,太阳欲沉不沉。
龙泉村的社火与别处的社火不同,它没有高跷、旱船、秧歌之类,倒是有“九曲黄河阵”和“十殿阎罗”。直到夜幕降临,一个老农在与“九曲黄河阵”对称的空地上画一些我看不明白的图形,听乡亲们解释,我才知道这是地狱图,传说中用来释放十八层地狱的鬼。等晚上十二点以后,响工吹过乐、和尚念过经、在引导幡的引导下,十八层地狱的鬼就能全部被释放,是龙泉不是龙泉的鬼都能来龙泉过个年。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世面。我惊呆的不是地狱图,而是地狱图居然是释放十八层地狱鬼魂的路径;我惊呆的,是龙泉人不仅仅释放龙泉的鬼,而是所有的鬼;我惊呆的,是龙泉人说的人鬼不分,这是给了鬼多大的尊敬!那一刻,我脑后起了风,风从两耳飒飒吹过,鬓边的头发被风张得笔直。我强烈意识到这是个小说,我下了个硬决心,一定要把这写成小说,不管笔力够不够。
山西晚报:再回到这部作品上,“我”肚里有个不想生出来的孩子,具体是想表达什么?
苏二花:
在小说里,“我”肚里有孩子,“我大哥”患病。但是该生下孩子的不想生,该安详死去的不想死去,这是这个小说的命题,它的作用是推动小说一直往前走。最好的小说应该是写人的问题,但小说不解决问题,把问题用很好的语言呈现出来已经足够。解决问题,那是读者的事。
“禳”,是祈祷,消除灾殃 “禳瘟会”是地方风俗,反抗瘟疫
山西晚报:具体说说“禳瘟会”吧。
苏二花:
禳瘟会是娄烦当地的传统节日。为了写这个小说,我采访过很多人,也查看过《娄烦志》和《娄烦风俗》以及其他众多资料,都没能找到这个节日的起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故事或人物。没有确切资料与采访为根据,我不能做出更多解释。
从古至今,瘟疫都是人类面临的重大灾难之一,在没有科学技术去解释和解决之前,人类对待瘟疫的态度就是敬畏。不但娄烦,我国各地都有与瘟疫相关的传统节日,只是叫法不同而已。而娄烦龙泉村把“禳瘟会”这样的节日放在一年起始,足见对瘟疫的重视和忌惮。
“禳瘟”的“禳”,名词解释是向上天祈祷消除灾殃、祛邪除恶的祭祀。娄烦龙泉村的“禳瘟会”,把给活人走的“九曲黄河阵”和给亡故人走的“地狱图”放在对称的位置,里面包含着敬畏,但更多的还是豁达和不屈吧。具体到小说里,“禳瘟会”是达到用传统节日完成对人的救赎。
山西晚报:一说地狱,让人觉得很沉重。小说中的父亲为什么要画地狱图?
苏二花:
画地狱图就像垒旺火、放鞭炮一样,是娄烦过年的传统。具体到小说里,父亲画地狱图,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死的豁达,这豁达不是父亲独有的,而是属于整个龙泉村的,属于我们传统文化体系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
山西晚报:写这部小说,从个人角度说,主要想表达什么看法?
苏二花:
还是那句话,想表达人的力量。世事不如意者常八九,我们存活,总有那么多是违背我们意愿的,那我们有能力反抗吗?对传统节日仔细盘点,竟从其中都找到了反抗的依据,原来我们传承的,一直都是反抗。《社火》里的“禳瘟会”是传统节日,它反抗的是死亡和疾病,它是要把所有亡故的鬼魂都释放出来,与活着的人一起共度佳节。我相信这种力量一直存在,并且有仪式感。
虚构是小说最大的特点 深入龙泉村,是让作品更接地气
山西晚报:小说中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有体现吗?
苏二花:
小说是虚构艺术,出自生活,加入作者对世界的认识。
山西晚报:小说中的人物,比如“大哥”“父亲”等在现实中有原型吗?
苏二花:
虚构是小说最大的特点,也是小说家的艺术所在。如果读者读完小说后,会觉着小说中的人物真的存在,或者一定有原型,那说明我这个小说写好了,我的小说艺术成功了。
山西晚报:写这部小说,您去了几次龙泉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苏二花:
前后去过两次,那里距离我居住的地方还有百十里,并且没有公交车,我必须把准备工作做充分,这样写起来才更接地气。
一个月后,朋友陪我二去龙泉,约了静游镇中学的栓亮老师。她也是我的一个朋友,我们一起找到了龙泉唯一会画地狱图的张继元老人。张继元70多岁了,身体健康,耳聪目明。对老人的采访很顺利,只要肯问,他就肯答,还拿出九曲黄河阵的图谱给我们耐心地讲解。
小说写了一半以后,朋友又陪我去了娄烦民俗作家张贵桃老师家,对龙泉以及娄烦的民俗做了进一步了解。张贵桃老师赠给我一本《娄烦民俗》,对我帮助很大。
山西晚报:采访过程中,有什么感触?
苏二花:
感受比较大的是,当时现场没有人知道“地狱图”到底是什么,而这正是有趣的地方。不知道无非有两点:一点是真不知道,一点是知道也说不清。小说的使命不正是在这两点之间寻求立意吗?那我就采访知道的,说出说不清的那个部分。
山西晚报:这部小说介于乡土和城市题材小说之间,和以往的小说写作有什么区别?
苏二花:
我觉得这个小说的核心还是在城市。“我”和“我大哥”都是在城市受伤,然后回村去疗伤。另外,我个人觉得作家不应该简单地把小说定位成农村题材或者城市题材,好小说应该是出得去,回得来,农村或者城市不过是小说的背景和人物活动的场景。
山西晚报:《社火》的语言很有特色,就像黄土高原的风一样,刮得利落还很厚实,是刻意这么表达的吗?是否受到哪派风格的影响?
苏二花:
没有。对我来说小说就是日常体现,我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风格,在我看来,小说作家的风格就是自己的性格,而性格是独有的。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但性格不是。我见到太多人,不但把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也把自己的性格艺术化,这样做挺圆润的,但是不好。对一个写作者,尤其不好。一个作者如果没有自己的性格,那很难有立得住的作品。
从网络写手转型为传统作家 除了小说,还创作儿童文学
山西晚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写小说的?
苏二花:
从小就喜欢。最早的小说是初二写的,500字。如果一个小说作家能说出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小说的,那他一定不是真的喜欢。真的喜欢,从来不是按时按点到来,是突然袭击,或是点滴渗透。我早年在代县运输公司工作,体会到了日常百姓生活的种种,这些经历促使我创作时很接地气。点滴渗透,是说这个意思。
山西晚报:小说写得好的人,大概是个人的故事比较丰富,谈谈你的经历和小说之间的联系。
苏二花:
人生故事丰富的,不一定能把小说写好。写小说靠的是感悟力和灵性,有能力把小说从丰富的故事里摘出来,并加以放大,这才是好的小说作者。小说不等于故事。
山西晚报:这个时代,您认为该给读者奉献什么样的作品?
苏二花:
起码该让人感受到善意吧。我在和孝义市的作家们交流写作心得时说过三个善良:一是写作善良,就是不要把小说写得深奥难懂,不要云蒸霞蔚让人摸不着头脑;二是对笔下的人物要善良,要给人物光和出路,不要把人往绝路上写;三是作者本身要善良,要怀有慈悲心和救赎心。原话记不住了,大致是这个意思。
山西晚报:您原来是个网络写手,怎么想到转型了?
苏二花:
颈椎受不了。网文要求日更3000-6000字,我能写,可我颈椎受不了,只能改写传统小说。
山西晚报:说说当初在网络上创作小说的经历。
苏二花:
网络小说,我最好的成绩是起点中文网女生频道新人榜第三名。而且我只要投稿,网站一定会和我签约A级作家。但我没有坚持,因为身体原因。
为了冲榜,我从每天3000字加成6000字,后来又加成每天9000字。这需要好颈椎来支撑,写网文不缺故事,缺的是好颈椎。
山西晚报: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在你看来主要有哪些不同?
苏二花:
我认为最基本的不同是,一个发在网络上,一个发在期刊上。都不容易,各有各的难。把稿子投到期刊文学,大部分是没有回音的,每一个知名作家都是从投稿的煎熬中走出来的,一言难尽。而网络文学需要写大量创意好的文字,能吸引住读者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些所谓的大神级作家,没有几千万文字做基础是上不到那个位置的。
山西晚报:除了小说,还写什么体裁的作品?
苏二花:
除了小说,还写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大道至简大概就是指儿童文学,但愿我能把儿童文学写好。



